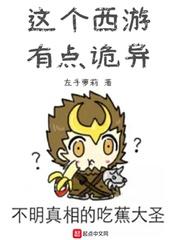456小说网>非典型炮灰 [快穿 > 第23章 爸爸(第1页)
第23章 爸爸(第1页)
暴雨如注,雷电轰鸣。
当路德维希带着浑身湿气赶到医院时,公爵和玛蒂尔达已经到达现场,他们身上都还穿着白天参加海兰德总督葬礼时的黑色制服,出现在医院这种场合时,无端让人心里生出一股寒意。
医院和丧葬服,这会让人联想到极其阴暗恐怖的事情,比如死亡。
路德维希是从一场军事研讨会上匆匆忙忙地赶过来的,他来得匆忙,身上的那件黑色长风衣外面全是水,衣摆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落在大理石地砖上。
到达现场后,他死死地盯着抢救室外的红灯,医院的消毒水味刺得他鼻子生疼,雨水带来毒蛇般的寒意,医院走廊的气氛也因为他的到来变得肃杀冰冷。
因为长时间不眨眼,他感到那只黄金义眼发出尖锐的疼痛,抢救室内的医学仪器又不停地发出嘀嘀的叫声,让他一阵阵耳鸣。
他想起几年前在翡冷翠时,他也是这样守在医院抢救室的门口,心焦如焚地等待着。
即使强势如他,在死亡面前,依旧无能为力。
看到路德维希从凯撒大宫殿上赶过来,公爵上前对他说明情况:“是在皇后大道那边遇到的刺客,嫌疑人已经被禁卫军当场拿下,你弟弟他……”
接下来的话公爵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子弹直直地射入拉斐尔的胸口,送到医院时已经失血过多,医生还在里面抢救,但听主治医师的语气,似乎情况不怎么乐观。
公爵犹犹豫豫地看向路德维希紧绷的面容,到底没敢多问,自从路德维希成为将军后,他们父子之间早已不是无话不说的状态,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路德维希在暗地里在策划什么,再说雪莱还在旁边呢。
雪莱失魂落魄地坐在抢救室外面的椅子上,他的耳朵已经让护士消毒包扎好,子弹只是擦过他的耳廓,伤势并不严重。
他低着头,双手颤抖地握住胸前的十字架,苍白清透的唇不停地阖动。
这是在诵读经文为拉斐尔祈祷。
他黑色的制服外面留有大片大片的血迹,有他自己的,也有拉斐尔的,彼此的血就这样纠缠在一起,分不清到底谁是谁的。
路德维希迟钝地转移目光,看向坐在安然无恙的Omega,他看上去那么纯洁干净,没有沾上一丝俗世的污浊,和自己完全不一样。
他的弟弟就是喜欢这样纯洁柔软的Omega吗?
从来,从来没有那一刻那么厌恶过一个人。
路德维希清俊的面容扭曲起来,他一把扯过雪莱的衣服,粗鲁地将他从座位上提起来,逼问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是拉斐尔躺在里面。”
迟钝的雪莱并没有听出路德维希话中的机锋,他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面对路德维希的质问,他眼神空洞:“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丧礼结束后我和拉斐尔一起回家,雨下得实在太大,我们没办法只好躲雨,不知道怎么的就听到枪声,他把我推开,自己却………”
说到这里,他语气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他也是看到拉斐尔倒下后才意识到那不是鞭炮声,是枪声。
他呆在教会学校过上十几年的封闭生活,竟然连枪声和鞭炮声的区别都分不清,平生第一次,雪莱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
路德维希痛苦地闭上眼:所以,是拉斐尔发现有狙击手,才把雪莱推开的?
就是因为眼前这个东西?
路德维希睁开眼,猩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眼前的Omega,似乎非要从这张脸上看出些超凡脱俗的东西,但他什么都没看到,只是淡金色的卷发,满是泪水的墨绿色眼瞳,一张懦弱愚蠢的脸。
见他一副要吃人的模样,一旁的玛蒂尔达冷嘲热讽:“你怪他有什么用?”
她抬起手腕轻轻地按了按头上的那朵白色的山茶花,笑容森冷:“谁造成的这一切你心里清楚得很。”
路德维希身体一僵,慢慢地松开雪莱的衣领。
失去他的力度,雪莱直接脱力地跌倒在地,他呆呆地望着抢救室的门,眼泪忍不住流出来。
路德维希再也没有搭理他的想法,在注视那盏红灯一段时间后,他疾步往前走去,背影歪歪扭扭,康拉德连忙跟上去。
终于到达没有外人的楼梯道后,路德维希关上安全通道的门,然后像是卸下所有的伪装一样,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他原本挺拔的肩膀不住地颤抖,身体无力瘫软地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一只手死死地扣住墙壁,手背青筋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