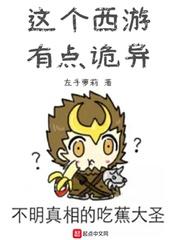456小说网>非典型炮灰 [快穿 > 第93章 十面埋伏2(第1页)
第93章 十面埋伏2(第1页)
“小如意,你是自己束手就擒,还是要逼我亲自来捉你?”
薛平津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上,扬声劝降,他今日身上是件绛紫色的骑装,头戴束发紫金冠,外披蟒纹明光甲,原本阴柔的相貌在这身装备的修饰下也显得迥然独秀,气宇轩昂。
“我可以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考虑,哈哈哈,不过,你是绝对逃不掉,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哈哈哈。”
他向来是得志便猖狂的性子,眼下率领几千铁甲骑兵包围住崔遗琅一行人,见他们只有几十名轻甲骑兵,还带有两个累赘,便觉得胜券在握,肆意张扬的笑意回荡在狭窄的山谷中,尖锐刺耳。
黄昏将至,沸腾的红日悬挂在旷野的地平线上,天穹被火烧云晕染成刺眼的猩红色,列队整齐的骑兵的影子被夕阳无限地拉长,他们身上的玄铁铠甲上折射出阴冷的寒光,赤色的战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
薛平津一个抬手,一时间鼓声大举,震天撼地,步兵方阵看到旗手的指示,开始以令人窒息的气势朝崔遗琅一行人逼近,将他们重重包围,步兵用手里的铁刀敲击盾牌,铺天盖地的喊杀声让崔遗琅身下的骏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显然也感受到面前的杀气。
“将军,我们该怎么办?”
身后的骑兵们见此情状已经开始沉不住气,焦急地出声询问。
崔遗琅沉声道:“别慌,你们都是军中精锐,当初也是经过重重选拔才成为我的属兵,薛平津不过一介莽夫,排兵布阵远不如他哥哥,若是只求脱身,未尝没有生还的机会。”
他认真观察敌军布阵的破绽,果真发现西南角的包围网要松散一些,心下已然有了主意。
在崔遗琅这样一番话的激励提醒之下,身后的亲卫兵们因为敌军人多气盛而生起的退却之意渐渐消退,他们看向这位年少成名的小将军,只见他面容沉肃,眼神坚定,丝毫不见退却之意。
他们猛然想起,当初这位小将军出行在外,也曾经以一挡百地对战过薛家军,有他做领头,说不定大家伙儿还能有一线生机。
其中一位叫林忠的亲卫兵声音坚定地附和道:“投降是死,不投降也是死。薛平津那竖子小小年纪,恶贯满盈,跟他那个哥哥一样为非作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诸位兄弟们若是落到那小子手中,那定是生不如死。不如和崔将军一起,大家合力杀出一条生路来。”
他这样一高声附和,也带动其余士兵附和道:“对,跟他们拼了!”
“妈的,老子的家乡就是让薛家那俩兄弟屠城的,老子绝不投降,新账旧账一起算,定要叫薛平津这黄口小儿好看!”
“跟他们拼了!”
崔遗琅不由地松了一口气,能激起斗志肯定是好的,虽然他心里也没有把握能杀出重围,但他身为将军,绝对不能露怯。
林忠又问道:“将军,你有什么法子能助我们冲出重围?”
见手下打起精神,崔遗琅提出自己的办法:“我观西南角的兵力要薄弱一些,现在的唯一的办法集中我们所有的兵力朝西南一角进攻,将他们的防线撕破一道口子。等下我打头阵,你们紧跟在我身后,一起杀出生路。”
诸位将士们闻言都高声附和道:“好,那就依将军所言,杀出生路!”
周梵音亲眼看见崔遗琅短短几句话便激起众人的求生意志和斗志,又见他肤色白皙,面容秀丽,俨然有副美少年的姿容,但他眼神却里有股野狼一样毫不驯服的倔气,漆黑的瞳孔里光芒四射,满脸肃杀之气。
他心中一荡,从尾椎骨处涌上一股莫名的悸动,连骨头缝里都一阵酥麻。
可是想到这桩祸事是因谁而起,周梵音难免心生愧疚,他抱紧怀里的小世子,轻声道:“对不起,都怪妾身不好,若不是妾身赌气出走,也不会让诸位将士落入薛家兄弟的圈套里。”
林忠冷笑一声:“哦?恕末将冒犯王妃,只是事情太巧,让人不得不起疑,莫不是娘娘与薛家兄弟联合,想骗将军出城,所以才害得我们落到这个境地。你身为姜家妇,为何要帮助外人陷将军于不义?”
说到最后,他已经是疾言厉色,诸位将士们也面露不快,显然对这个王妃没什么好感,王妃身为薛焯的表妹,难免怀疑是不是她通敌。
周梵音不过多辩解,只是一副怯弱的模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又不是薛焯的嫡亲表妹,同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薛焯还将周家夷灭三族,我怎么还会再为虎作伥?”
念及周家几乎满门被屠,诸位将士们这才回过味来,心里的疑虑消散不少,最后还是崔遗琅解围:“好了,眼下不是争执的时机,还是简单商讨出个方案,杀出生路要紧。王妃的事,回到王府,王爷自有定夺。”
他见周梵音脸色苍白,看向他的眼神无措又愧疚,哪里还不明白其中的渊源,他心中一叹,却只是道:“娘娘,您也别多想,现在最重要是杀出生路。得罪了,待会儿您得和我共骑一匹马,我带您和世子冲出去。放心,我会保护你的。”
周梵音只是摇头,他迟疑地想说什么,但在看到崔遗琅那双漆黑的眼眸时,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或许他是在害怕,害怕自己说出真相后,这个承诺会保护他的少年会讨厌自己,他从来不在乎旁人的看法,如今却是第一次有了顾忌和在乎的人。
从坚固的防线中杀出重围已是不易,更何况还要带上手无缚鸡之力的周梵音和小世子,但崔遗琅一向是良善纯稚之人,别说这是姜绍的王妃和儿子,就算她们只是无辜牵连其中的妇孺,崔遗琅也不会丢下她们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