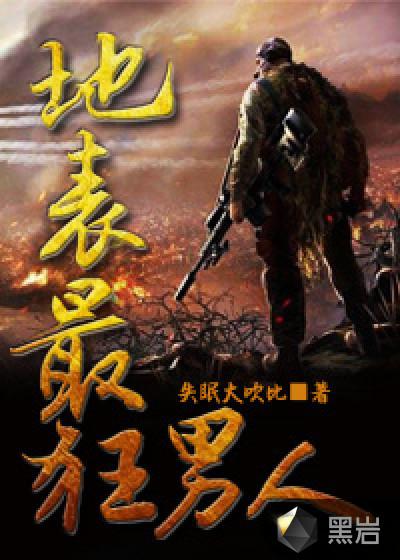456小说网>看透爱情看透你云菲菲 > 153不需要别人只要有我(第1页)
153不需要别人只要有我(第1页)
她坐起来,环视一圈,确认自己的确正睡在一个帐篷里。
似乎是怕她冷到,她明明都睡在睡袋里了,外面还多加了一层被子盖着。阮舒将自己解开来,发现身上穿的是睡裙。
“……”
由此更加能够确认,自己现在应该正和傅令元在一起。
拉开门帘,阮舒先探了半个身体到外面查探。
照明灯照出帐篷搭在一棵树底下,周围是一小片的空地,空地之外的三面包围的全是树林。
阮舒从帐篷里出来。
仅一面为空旷的视野,越过山体轮廓,隐约可见城市璀璨而浮华的灯影,遥遥的灯火成片,如同自山前淌过的细河。
再过去,则是偶闪灯塔亮光的此刻看起来乌漆墨黑的海面,与漫天的星光连接,仿若一体。
傅令元正面对着城市的光影和海面的辽阔坐在折叠躺椅上,手边是一张小桌子,桌子上很随意地放了些许吃食和啤酒。
背影在缓缓的夜风吹拂之中愈显挺阔,独自一人,仿佛凝聚了此时世间所有的孤独与寂寞。
阮舒站定在原地,视线静默地凝注在他身上。
不消片刻,便听他用背影沉声道:“过来,不要站在那里吹风。”
阮舒行至他身侧。
傅令元正在抽烟。指间夹着的半截尚在燃着,脚底下则散落着烟蒂,乍一看,有点数不清楚数量。
因为她的到来,他猛地最后吸了两口,便将烟丢地上,用脚尖碾灭烟头的星火,然后抬眸对她伸出手。
本就湛黑的眸子此时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深沉,和他此时周身所散发的感觉是一样的,然而他的眼里依旧对她含着笑,唇角亦斜斜地噙了抹笑意。
阮舒将手放在他的掌心,即刻被他的熨烫所包裹。他轻轻拉了她一下,她会意,侧身坐到他的腿上,靠上他的胸膛。
他带着糙茧的指腹摸上她的左手手腕,摩挲那抹梵文画符:“什么时候弄的?”
“千佛殿的山上。”约莫是在这外面坐太久的缘故,他的指尖难得地有点凉,令阮舒感到一瞬间的战栗。
之所以说难得,是因为印象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总能保持体温的熨烫。即便冬天很冷的时候只穿一件薄薄的风衣,即便是落河在水里泡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冷?”傅令元立马察觉,摸了摸她身上的睡裙,“外套就在睡袋旁边,怎么不穿出来?”
“没有冷。”阮舒的手臂圈紧他的腰,更加紧密地偎依在他的怀里,“三哥抱紧我就可以了。”
傅令元轻笑,稍低头,下颔贴在她的鬓边,继续摩挲她的手腕:“梵文写的什么?”
阮舒怔了一下,才想起来:“我忘记问了。”
语气携了些许的懊恼。是以往的她并不会有的情绪。傅令元不禁勾唇,又问:“为了遮盖伤疤?”
“嗯。在千佛殿后面的小广场,刚好碰上有个沙弥在画符。好像是颜料比较特殊,不会掉色,所以就用一只孔明灯的香油钱,弄了这个画符。”
“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用刺青来盖伤疤。”
“三哥要是每留一处伤疤,都去刺青,那现在身上应该满满的全是符纹。”说这话的时候,阮舒的脑海里已在自发脑补他浑身刺青的模样,竟然觉得可能会挺酷的,笑了,“那就更像古惑仔了。”
“嗯?‘更像’?”傅令元敏锐地揪住她的措辞,“在傅太太的眼里,原来我一直都是古惑仔。”
“难道不是么?”阮舒故意反问,想起一件旧事与他提及,“三哥以前在和显扬一起在看《古惑仔》的整套碟时,不就以陈浩南自居,说显扬没资格当你的小弟。”
傅令元似忖了两三秒才记起:“你说那个时候啊……”
他拖着长音,隐隐拖出一丝暧昧的意味。
阮舒正狐疑,便听他的嘴唇贴在她的耳廓旁,低低道:“那一次事情的重点,好像应该是,你推门进来时,电影里的画面恰恰在上演十八禁。显扬生怕你误会我们在看A片,所以慌里慌张地解释。”
阮舒:“……”
她自然记得。
严格意义上来讲,算不得十八禁,只是对于彼时他们的年龄,稍微色、情暴力了些,还被她撞见,于是唐显扬特别地紧张,解释了一番电影的内容,担心她不信服,拉上傅令元为他佐证。
可其实,她当时并没有觉得太怎样。而且她察觉到了,当时傅令元也和她一样没有觉得太怎样。只有唐显扬太单纯了些。
“你那个时候,和显扬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傅令元忽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