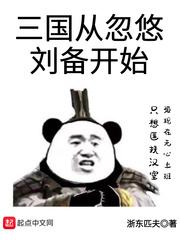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贵女长嬴讲什么 > 第七十九章 久违之名(第1页)
第七十九章 久违之名(第1页)
到得后日,木春眠果然携了赖大勇至明沛堂求见。
卫长嬴刻意拿架子,足足晾了他们好半晌,才允他们入内。
等两人进了门,卫长嬴眼风一扫,见木春眠风尘仆仆的,似乎不及前往季园梳洗,就直接抓了赖大勇过来了。再看赖大勇——这是卫长嬴头一次见到这声名在外的私盐贩子,从屏风的缝隙里望去,此人与传闻里一样,生得魁梧健壮,皮肤黝黑,脸上还有一道两寸来长、半寸来阔的伤疤,犹如蜈蚣一般爬在颊骨上,望之狰狞可怖。
这副说他不是土匪都没人信的尊容,偏作讲究和气生财的商贾装扮,怎么看怎么别扭。
只是这赖大勇虽然看起来剽悍得紧,此刻却满脸堆笑,一副讨好的样子……让卫长嬴留意的是,他这副讨好不太像是冲着自己来的,倒仿佛是冲着木春眠去的。
想起曹丫对赖大勇的称呼,卫长嬴觉得很有意思:这赖大勇看年岁约莫是三十有余,联合季固的年纪……
她也不说话,任凭下首木春眠与赖大勇恭恭敬敬行了礼,却不闻叫起之声,就那么尴尬的立在下头。
一盏茶、两盏茶……卫长嬴好整以暇、慢条斯理的喝到第三盏茶,手边的点心也换了好几轮了,下首一直维持着行礼姿势的木春眠与赖大勇额上都有些见汗。
只是偷眼上窥,却见因为赖大勇这外男而特意设起的薄薄的细绢屏风后,从轮廓也知裙钗雍容的贵妇人似低垂着头,看着伏在自己裙边的花狸猫,低笑着问左右:“它怎么跑这里来了?时雨也不看好了它?”
一个粉衣小使女小心翼翼的道:“回少夫人的话,婢子一直带着小花呢。只是小花就爱到处乱跑……婢子上回看它爬在花丛里,想抱它走,差点被它挠了一爪子!”
“难道是我上回给了它一块腌鱼,叫它惦记上那一口了?”卫长嬴失笑,朝那花狸猫略一伸手,那猫就乖巧敏捷的跃上她膝,伸着脑袋在她掌心蹭了又蹭,发出低柔的叫声。
“小花就是喜欢少夫人……”
主仆说说笑笑,俨然堂下根本没有木春眠与赖大勇这两个人一样。
见这情形,木春眠咬了咬唇,却还是忍住了。
但那赖大勇久为悍匪,脾气暴烈,忍耐这良久,到此刻却有些按捺不住,忽地直起了身,大声道:“老子……在下日前拜见沈三公子时,多有卤莽,今日特意前来向少夫人赔罪!少夫人若是心头有气,在下任打任杀,绝无二话!少夫人这样晾着在下,却又是什么意思?”
这厮发作的突兀,卫长嬴因为晓得沈藏锋是要蒙山帮的,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就借这个机会把那叫小花的花狸猫交与时雨带出去,慢条斯理的道:“赖帮主这话说的奇怪,我一个妇道人家,今儿个还是头一回见着帮主,却与帮主又有什么冤仇,需要拿帮主出气呢?”
“在下推荐了在下的妹……”赖大勇话说到一半,自屏风的缝隙里,卫长嬴很清楚的看到木春眠转过头去,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这一眼顿时叫那悍匪噤了声,嘟囔几句,才讪讪道,“总之在下就是错了。”
卫长嬴道:“纵然赖帮主犯了错,又与我何干?”
“……在下冒犯了少夫人。”
“我从未见过帮主,帮主如何冒犯了我?”
就着这个话题推来推去良久,那赖大勇郁闷得几乎吐血,暗道与这些娇生惯养的大家贵妇说话就是累。他索性眼一闭,道:“日前所提之事,乃是在下一人所为,与在下的义妹毫无关系。少夫人……”
“义妹?令妹是谁?”卫长嬴打断了他,“该不会是木堡主吧?”
不想赖大勇居然当真点一点头
:“在下生身父母早已过世,曾在山间蒙义父搭救,是以结下父子缘分。春眠自是在下的义妹。”
屏风后,卫长嬴微一蹙眉,心想前日沈藏锋也没细问,还是没问或者问了没告诉自己?这赖大勇之前一直托季固那边传信,只道是蒙山帮跟曹家堡关系匪浅,如今看来,却是他自己跟季固关系匪浅。
原本季固一个外人,非但在曹家堡立足,甚至还鸠占鹊巢的让自己的女儿、外孙女都占了堡主、少堡主之位。无论沈藏锋还是卫长嬴都猜测他手腕过人,又有一手绝妙医术,现下才晓得,季固气运也不差……在山里救个人,居然还救成了蒙山第一帮的帮主。
有这么个强援,何愁控制不住不过是流民聚居的曹家堡?
想到这儿,卫长嬴心念一动,就道:“原来你还是季老丈的义子?真是叫人意外。”
下头赖大勇跟木春眠等了片刻,却不见她再说什么,都觉得有点骑虎难下,木春眠就出来解释:“少夫人,日前家兄为人所激,故而向沈三公子提出纳妾之事,实际上却是另有缘故,此事须不敢瞒少夫人……”
卫长嬴慢慢呷了口茶水,才淡淡的道:“缘故?只是不管什么缘故,想来都是公事,却又与我一个后院的女流之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话你们该去向我夫君说才是,与我说了,何啻于对牛弹琴?”
木春眠赔笑道:“少夫人您不知道,这事儿半公半私的……小妇人嘴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总之这突如其来写信与家兄的人,虽然本身名不见经传,但幕后似有高人。只是家兄未肯投奔他们,所以一直不知那幕后之人是谁。然据家父推测,当也是海内六阀之一……尤其这招揽家兄之人用兵精妙,家兄数次败于其手,却得对方次次手下留情,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