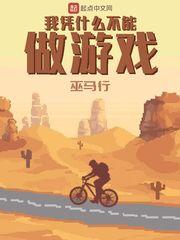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穿越到古代王府后成王妃 > 第六十七章 吃面看戏(第2页)
第六十七章 吃面看戏(第2页)
二十余名手执水火棍的差役,经由三面,朝酒楼飞奔。
头目一声令下,差役们如潮水涌入。
很快,酒楼里响起了声音,有冰火棍杖责,有哀嚎求饶,有鼓掌交好……
片刻之后,方才意气风发的二锤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被押着出来。
头目手中攥着一把铜钱,还有小粒碎银,面露嫌弃,默不作声地揣入衣袖。
“这点儿家当,也敢妄论国朝!”
酒客们随后走出,各自双手环抱,全是看戏的模样。
平日与二锤子交好的,倒是会惋惜几句。
“倒霉的家伙,好不容易赚了点,又没了。”
惋惜归惋惜,却没有担心二锤子出事。
说到底,他只是嘴碎了些,罪不至死,吃点苦头就又出来了。
像二锤子这种,时不时发些小财的,衙役们乐见如此,毕竟能平添些油水,贴补家用。
李常笑恰巧吃完了面,整理衣袖,再度走出。
“这人间百态,倒也有趣地紧。”
“平日里,还需多来几回。既不贪嘴,也不贪八卦,而是胸中蕴有一口正气。此等犯纪之徒,当需批判!”
心想着,李常笑的胸膛挺得更直了。
路过一家青楼,他按住下巴。
却是犹豫酒饱饭足后,要不要也进去批判一番。
很快,他转头又走开。
“日子还长,至少现在无意。或许日后,汴梁盛景,才子词赋可引我再来。”
“金樽清酒,十街词客。”
夕阳下,一江孤舟远远驶去。
建宁元年,十一月。
长安。
随着义军声势浩大,建宁帝也从中看出了些许疑窦。
明明只是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即便一朝举起兵器,却无法改易本质。
平叛大军征发数月,损失不少,却也未能彻底平息动乱。
义军中有高人!
想到这,建宁帝不由眯起眼。
“图谋我大汉,当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他两手伏于案前,面露思索。
这领兵的将领,又该是何人。
忽然间,一个人名映入脑袋,身经百战,老骥伏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