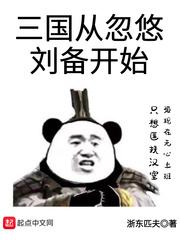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苔组词 > 第二十八章(第1页)
第二十八章(第1页)
马车停稳,沈澈从车上下来,敞开自己的披风,露出隐在下面的青色官服出来。
沈澈苦笑一声,对已经反应过来自己就是查出他那可笑的二十两贪墨案的巡按的牧青远说道:“绸琼知县牧青远,你理应在牢中等待朝廷的发落。本官问你,你现下为何带人在外游荡?”
牧青远电光火石间想到先前祖重南的提醒,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抓住自己这点纰漏的竟是一起醉酒过的同届,他愣了下,翻身下马对沈澈行礼道:“下官知罪,见过沈按台。”
旧时临屋的两人相对一时无言,最后是牧青远莫名有些想笑,没忍住笑了出来。
沈澈看着他笑的很是开心,又是长长一声叹息。
等牧青远好容易笑够了,才对沈澈说道:“沈按台,寒舍是去不了了,下官现在暂住牢内,你可要去那一聚?”
于是本来就有些寒酸的绸琼寒酸的牢狱内,灯火摇曳后的草塌上,坐了两个叙旧的大人。
“顷碧你刚刚在车内,其实早就看到我了吧?”喝了口热茶暖身,牧青远问他。
沈澈没答话,笑了笑说:“若你没看到我,直接回牢里就好了。”
“从一开始发配到这鬼地方时我就发现了,我运气差些,”牧青远摆摆手表示不说这些,他问,“顷碧你不是去翰林院了么?怎么这么快就有了巡按这么个好差事?”
“说来话长……”沈澈不想提,只说了四个字就停了下来。
牧青远看出他的意思,道:“那就长话短说,若是短话说不明白,就别说了。你既然来了明月郡,从我这走时可以去韩绰那里看看,他来这儿饿瘦了不少,身姿是比之前有几分贴切他那个风姿无限的字‘熙色’了。”
说起旧友气氛轻松起来,两人聊了聊闲话,牧青远看天色不早,让沈澈在雪大起来回去。
沈澈看两人四周没人,牢中的牢头离得也远,低声对牧青远说:“绸琼的银曹可是少了一块铸银的模子?”
这事昨日孟冠才查明白,牧青远惊道:“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沈澈说:“那块模子在景州,搜朱虬的家时搜出的,我已差人送去了芍阳。我走后,你莫忘上书朝廷,说那模子是你来绸琼时就少的,听明白了么?”
牧青远其实打定主意不去问沈澈有关这贪墨案的事,现在对方自己提了出来,忍不住问他:“…………那二十两银子是怎么回事?”
“哪里是二十两,”沈澈压低了声音,“我查到的是五百两绸琼官银。”
牧青远愣住了,既然查到了五百两,没道理传到自己这儿时变成了二十两,他心下了然,对已经站起身准备走的沈澈说:“顷碧,你不该帮我遮掩那五百两银子……”
沈澈瞪他一眼:“你以为我想惹上麻烦?炭资银子虽在官场中司空见惯,五百两作为贿银说多也不多,但凭借此也能要了你的命。”他推开牢门,对牧青远先道了原本明日才应该道的别,“我今日一到就抓你个私自离狱的现行,留在这不知还有多少破事,明日就启程了,你在绸琼行事小心。”
牧青远没想到沈澈竟不在绸琼多留,隔着木栅对就要走入风雪中的沈澈不舍道:“重逢匆匆,好在今别有落雪如枝头梨花闹,也不算太寂寞。”
沈澈笑道:“人人都说落雪寂寂,只有你说热闹,真是看得开。”他冲着牧青远挥了挥手,“走了,来日再见。”
牧青远把自己挂在木栅上看着沈澈掩上了牢房的大门,抱着木头杆子想刚刚沈澈和自己说过的话,想到灯芯淹在灯油里灭了时,敲了敲门上挂的锁冲外面大喊:“牢头!牢头!!给本大人开门!!!”
牢头忙不迭的跑过来摸腰间挂着的锁:“大人怎么了这是?”
牧青远低头把批了一半的卷宗全部卷了起来,头也不抬的指了指地上:“这些被褥也都收起来。”
牢头站在门口看他蹲在地上七手八脚的收拾这些天他囤在牢里的东西,问:“大人你这是……”
牧青远把卷宗抱在怀里抬头对他说:“出狱!这个牢,老子不坐了!”
牧青远和江柳说过祖重南是他老师一事后,江柳就把祖重南从客栈接到了家里,吃穿度用都给的是最好的。
祖重南在松阳时就天天跑牧青远的小破院里蹭吃蹭喝,现在在学生家住着一点都没不好意思,他住的舒服极了,不仅住的舒服极了,还和家里的下人还有牧青远刚认的那个便宜儿子刘乙混的熟极了。
这日晚上吃的是江柳从山野猎户家中买的鹿肉,烤鹿肉活血补劲大的很,刘乙一直在床上翻腾到半夜都没睡着,偷摸着穿了袄子爬起来去敲祖重南的门。
“赤阳爷爷,你睡了吗?”
祖重南在写他的新话本,没睡,把孩子开门放了进来。
“赤阳爷爷,我想出去堆雪人玩,蔓蔓哥和大人都不让我玩。”刘乙的手好了不少,除了红看不出别的毛病,他故意不提自己手上的冻疮。
不知是不是因为隔代亲的缘故,皮猴子刘乙在祖重南眼里看着格外顺眼,祖重南一吹胡子:“雪都不让小孩玩了?不像话!”
所以等牧青远折腾完带着一堆东西到家时,推门看到的就是大半夜冻得鼻涕流下一道撅着屁股滚雪球的刘乙和他一旁站着折自己精心种在院子里假山旁的梅花枝准备给孩子堆的雪人做手的祖重南。
牧青远一阵邪火,插着腰气壮山河的冲着两人劈头盖脸一顿骂。
他这么一吵,整个牧宅的人都醒了,各个都披了衣服出来看,七嘴八舌的迎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