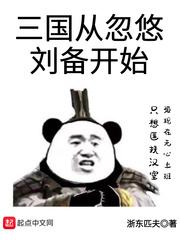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苔组词 > 第三十八章(第3页)
第三十八章(第3页)
不多久几月未见的昭勇将军季洺秋就骑马出门来迎,他看着本不应该出现在此的好友:“你不好好在你的苍州呆着,跑我这里来做什么?”
稽淮笑道:“不止我,赤阳先生也来了。”
季洺秋皱了眉:“师父也来了?”
稽淮点头:“来了,就在后面的马车里坐着。外面风大,冰天雪地的,还是找个合适地方好好说话吧。”稽淮似是真的怕冷的样子,说完这话就踩着踏凳上了马车。
季洺秋原本还想问些别的,他看着好友严丝合缝的车帘,一转马头将这一队人引向了自己平日里办公的军帐前。
季洺秋翻身下马,将缰绳递给来接的士兵,问正在下马车的稽淮:“你们这一队人来这要住多久?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几个营帐出来。”
稽淮摊了摊手:“多久我也不知道,说短五日就走,说长……说长大约有个十几日吧……”
季洺秋翻了个白眼:“连住几日都不知道,你到底来这干吗的?”
稽淮笑眯眯的答了:“来祸水东引。”
季洺秋刚舒展开没多久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什么祸水?”
稽淮没有回话,亲自去后面的车里接了祖重南下马,等三人都进了军帐避退旁人后,他才从袖中拿出了昨日收到的密函。
将密函先递给了祖重南,稽淮找了个椅子坐下,等着师徒二人依次看完。
看罢密函后,祖重南捋了下胡子先开口道:“此步棋着太险,不该由王爷行。”
稽淮坐在椅子上,右手的指尖不自觉的揉搓着左手的关节,说道:“是险了些,所以我将落子的棋盘放在了剑蓟。”
季洺秋阴沉着脸,冷哼一声:“此事若是做不妥当又被他人泄露出去,你可知我罪名?”
稽淮并没有十分理亏的样子:“我已知会过父王,将来事成最好,事不成也不会怎样。无非是海色郡,迟个几年收回来罢了。”
季洺秋眯起了眼睛:“‘事不成也不会怎样’?这话说的好听。”他话虽如此,但没有在稽淮将事端带到剑蓟这点上太过计较,“信上只说不日就到,可有那日苏到的确切时间?我好做准备。”
稽淮心头一轻,他知道是季洺秋答应了下来:“确切日子,还要等到今日傍晚的密函送到才能知晓。”
三人就这么在帐中又详谈了日后种种事宜,直到傍晚时才各自回歇息的营帐。
季洺秋路过嵇汀的营帐时看到里面亮着灯,问正巧从自己身边过的巡逻兵:“纪参军回来了?”
巡逻兵答道:“大约中午那会儿就回来了。”
他话音刚落,身旁的弟兄就冲着季洺秋挤眉弄眼:“将军,纪参军好像带了个面首回来。”
“嗯?面首?”季洺秋奇道。
他这么一问,巡逻兵们就笑嘻嘻的将嵇汀是如何用一辆马车拉回了一个熟睡着的清秀的男人的事讲了。
季洺秋听了一阵头痛,只觉得这兄妹俩真是自己命里躲不开的两颗灾星,他挥挥手打发了手下:“你们巡逻你们的,我去纪参军帐里看看。”他悄手悄脚的掀开了嵇汀营帐的掩帘,走了进去。
此时帐里的嵇汀并未察觉,她正和姜帆一起站在自己床边,看着睡得死沉怎么都叫不醒的牧青远小声嘀咕:“姜帆你蒙汗药下了多少来着?”
“什么蒙汗药?”季洺秋突然出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