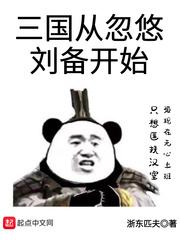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苔花 > 第十三章(第1页)
第十三章(第1页)
绸琼不大,牧青远从城西走到城东也只用了一个时辰。县城最繁闹的只有一条长街,剩下的都是一般的民宅,房屋样式越到县城边缘看着越简陋。
牧青远走到县城城门外,看着不远处的山川,对身边的江柳说:“我原想着在城里呆几日看看情况再上任,现在这城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再拖着也没意思,不如明日就上任吧。”
江柳应道:“听小少爷的。”
牧青远看天色不早,转身往城内走:“明日我去县衙上任,你去买两个下人,好照顾家里杂务。”
他正说着,忽然觉得路过的民宅中似乎是有人在看他。牧青远抬眼去看,看到一扇原本虚掩的门呯的一声关上了。
牧青远走着走着发现城郊这片地方,不仅是这扇门关了,自己所到之处,所有的门窗都关上了。
“呦,这真是有意思。”牧青远笑了,“这些县民看起来可一点都不欢迎我,和今早城门口迎我的人完全是两个意思。”
他说完这话一点也不担心自己将来处境,溜溜达达的走往菜市买菜准备回家做饭。
第二日牧青远拿着任书和官印上了任,所谓上任时新官要放的三把火牧青远没放起来,因为县衙中根本没多少人让他放火烧身。
牧青远在县衙里转了一圈,看着眼前零星几位的部下问:“绸琼的县丞呢?”
宋道答道:“回令尹大人话,没县丞。”
牧青远又看向典史问:“那县内的巡检呢?”
王大虎答道:“回令尹大人话,没巡检。”
宋道接话解释道:“绸琼地小,除了知县拢共就主簿和典史两个排的上品的官,”他说完这话顿了下又说,“嘿呦您看我这话说的,真算起来典史还未入流,就我一个有个九品的品级。”
“既然没巡检,那绸琼的巡防和缉捕盗匪由谁负责?”
王大虎回话:“都由典史带着的衙役负责。”
牧青远哦了一声,遣散了聚着的衙役,让他们跟着王大虎巡街去了。
王大虎出了县衙装模作样的走了一条街,看离衙门口远了,啐了口吐沫,朝着跟着自己的衙役挥了挥手:“滚滚滚,什么时候见老子正经巡过街,都给老子滚。”
衙役有些是临时抓来的县民,瑟缩了一下忙不迭的跑了,有几个在县衙混了有几年的衙役嘻嘻哈哈的和王大虎开了几句“是不是要找县南的席寡妇”这样的玩笑话,也散开了。
王大虎背着手原本想往家走,心里被刚刚几个衙役说的心痒痒,胯下发热,前面道路一转,往自己的姘头席寡妇家去了。
席寡妇守寡刚半年多,长相俊俏不说,床上也浪的起来,是王大虎睡过的女人中最能讨他欢心的一个。
寡妇家的小院木门虚掩着,里屋的门关的倒是死紧。
王大虎敲了敲门,在门外调笑一句:“娘子,开门了。”
向来见着他就像蝴蝶看到花一样贴上来的席寡妇没应声,王大虎又敲了几下门,一直无人应,他脾气一下上来,抬脚踹开了门,嘴里骂骂咧咧:“臭,大白天关着门,是不是背着老子我在家里偷男人。”
席寡妇没偷男人,她自己一个人穿着红肚兜仰面朝上躺在床上,一双平日含着春光的眼惨败如死鱼眼珠,一截洁白的小腿露在被子外面,挂在床沿上。
她死了。
当夜在县衙忙着看上一位知县留下的文书的牧青远回家吃了顿好饭,主簿宋道知道自己这算是应付过了新知县,也回家歇着去了,剩下的那个数得上名号的小县官典史王大花不在家,他扛着死了的席寡妇溜出了城,将人扔到了城外的半山腰草木繁茂处。
“呸!这倒霉娘们!”王大虎边抱怨边看枝叶是否遮盖住了死去的女人的身体。
下山往城里走时,王大虎忽然想小解,他解开裤子站在路边,骚臭的尿柱窸窣的浇在了地上。王大虎纾解完唱着小曲下山往家走,被他留在山上的尿液渗入地下,若有人心细仔细观察,便能看出这块留有尿印的地方,比起四周要高出一些。
牧青远在县衙看了一日的陈年卷宗,晚上饥肠辘辘的回到家以为有饭菜吃,就看江柳从正冒着黑烟的厨房里走了出来。
江柳看牧青远回来了,擦了擦手说:“小少爷,这边买不到下人,家务事只能咱们自己动手了。”
牧青远被呛的只咳,看了一眼厨房里:“你这是柴火放多了,出不来火,只能闷出来烟。”
江柳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我没下过厨。”
牧青远去房内换了常服,卷了卷袖子进了厨房:“你歇着去吧,以后做饭这事我来就好。”
他看了一天卷宗,现在生火做饭权当消遣。
绸琼不比松阳,饭菜中见不到一点油腥,当真是粗茶淡饭。牧青远一顿饭吃的食不知味,晚上在床上接连翻了半天烧饼才睡过去。
第二日他照常去县衙,因去的早衙役一个都未到。牧青远走近看到绸琼县衙的石阶上放了一卷叠起的麻布,他弯腰捡起来展开,有一个什么东西从里面滚了下来。
滚下来的东西是一节小指,包裹它的麻布上面是血写成的一个歪七扭八大大的“冤”字,“冤”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城外半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