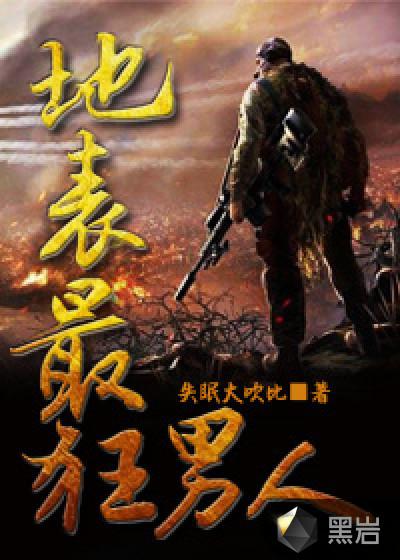456小说网>苔花 > 第二十五章(第2页)
第二十五章(第2页)
绸琼县衙现在运转正常,衙役基本上快招齐了,现在是临时让江柳当的典史凑合,想等培养出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再说。
接连几日处理了些鸡毛蒜皮的官司,今日官司少了些再加上主簿孟冠确实得力的很,牧青远清闲不少。
牧青远放衙后先去城北接刘乙放学堂,刘乙读书习字停滞了四年,现在混在一群七八岁的孩子里格格不入。
牧青远聘了辆马车带孩子往家走,看刘乙闷闷不乐:“怎么,在学堂里不痛快啊?”他也曾年幼过,稍微一想就知道刘乙哪里不痛快,“我和先生谈过了,若你进度快,先生讲的都能懂,就早早的把你调到中级班,你先忍个几日。”
刘乙一听有了盼头,眼睛一下亮了:“大人,我想吃酱肘子。”
牧青远笑了:“心情好了就想着吃,怎么光见你吃不见你长肉。”
刘乙捏了捏自己的小胳膊:“我这是竖着长,柳哥这几日还说我高了些呢。”他想起来自己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对了大人,柳哥字什么啊?我上次问他他不肯告诉我。”
牧青远乐了,他知道江柳一直不喜欢自己那个字,边笑边说:“‘烟柳蔓蔓垂’,江柳字蔓蔓。”
“江蔓蔓……这名字叫起来像个姐姐。”刘乙稍微品了下咂舌道。
说起来字,牧青远想起来什么问刘乙:“小乙你今年是不是满十二了?”
刘乙自己掰着指头算了算:“我虚岁已经满十二了,实岁还要等年底。”
牧青远看着孩子:“舞勺之年了,等年底过了生辰,就该给你起个字了。”
刘乙有些不好意思:“大人还给我过生辰啊?”
牧青远抱着手臂:“养了你哪有不给你过生辰的道理。不过这‘大人’二字什么时候改口啊,该叫爹了。”
刘乙叫不出口,他不好意思,正好西乡楼到了,孩子蹭的一下蹿下了车。
牧青远也不勉强,摇头笑了笑带孩子吃了酱肘子回家了。
江柳已经在家了,他现在还要充当绸琼的典史,分不开身,聘了几个下人正嘱咐他们平日里做什么,看到牧青远带孩子回来喊道:“小少爷,大少爷从芍阳来信了,还有几封从建德来的,我都放在书房里的信匣子里了。”
牧青远说了一声知道了,回房换了身轻便衣服去书房拆信。
牧青璞的信和往常一样,只是对他嘱咐,说来说去都是让他勤恳当官,莫要搜刮民脂民膏辱没牧氏门耀等等。
提笔给哥哥回了信,牧青远拿着裁信的银刀去开第二封信时,看着信封外熟悉的清丽小楷怔住了,身体比脑子更快的反应,眼泪瞬间坠了下来。
此时季洺秋一路风尘仆仆正好赶到绸琼,不顾江柳有些讶异的目光一扔缰绳问了牧青远现在何方就往他书房的方向走。
书房的门敞着,季洺秋脚步轻,走起路来并无声息,刚走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牧青远对着一封还未开封的信垂泪的模样。
牧青远对季洺秋的到来无知无觉,他正发怔,脸颊一热是有人帮他把泪拭去了。
“你不是走了么……”牧青远抬头看到季洺秋一愣,问他。
季洺秋没有回答,他俯身下来,抬起牧青远的下巴轻轻的亲了一口。
牧青远又是一愣,看季洺秋又想亲下来,偏头躲过了:“……我没这个心情。”
季洺秋知道他的推拒是因为那封信,一下发了狠,不管不顾的亲了上去,牧青远被他用双臂囚在椅子里挣脱不得,只能仰着头被迫承受。
唇齿纠缠间季洺秋嘴唇一痛,就尝到了铁锈味,他一路风尘而来,为的就是见这眼前人,现在看他反抗脑子轰的一热把人抱着直接扛回卧房直接扔到了床上。
牧青远半躺在被褥里被摔的有些发蒙,看季洺秋扑上来不管不顾的就要撕扯自己的衣服,不知道他这是发的什么疯,一咬牙也去扯他的衣服。牧青远被这么一主动季洺秋就更加起劲,顷刻间两人便纠缠在一起。
等到季洺秋这泄欲一样的床事终于结束,牧青远才终于得空强撑着自己的困意咬牙切齿的问他:“季西颢,你是不是吃了?这是发的什么疯?”
季洺秋仿佛现在才清醒过来,自己想了一路的话到了嘴边脱口而出却变成了:“我不要姑娘,我只要你。”
这话说的没头没脑,牧青远一愣:“什么?”
季洺秋把牧青远抱在了怀里,头埋在他颈肩又重复了一遍:“你听不懂也无妨,我一路跑回来,只是想告诉你,我只要你。”
牧青远心跳声骤然加快了,他说:“季西颢,你真是疯了……”
季洺秋贪恋的嗅着他身上的气味,闭着眼睛说:“我疯了,那你呢?你陪不陪我一起疯?”
牧青远一直想抓的东西现在就放在眼前,他却不敢要了。
季洺秋一直等到他以为牧青远是睡着时,才听他开口说:“我牧氏公子,身负百年家业,行有礼,举有制,伦常不可违,疯不得……”
季洺秋睁开眼睛刚想说什么,看到牧青远的样子话到嘴边哽住了,他把人抱在怀里,下巴轻轻抵着牧青远的发顶,叹了口气:“罢了,疯不得就疯不得吧……”
季洺秋说完肩头一热,他知道是牧青远的泪落了下来。
两人言至于此都再无话,听着窗外夏虫窣窣,相拥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