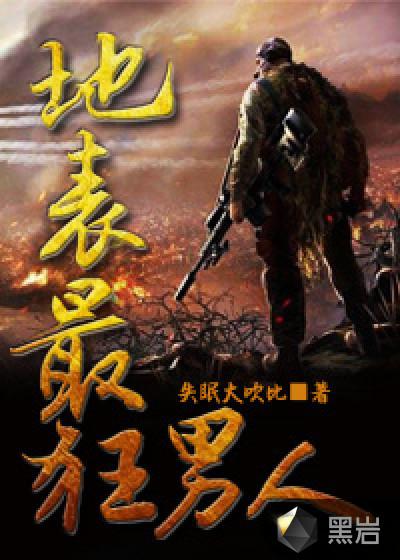456小说网>等到山河破碎什么歌 > 第一百零一章 韩大哥(第1页)
第一百零一章 韩大哥(第1页)
二人间或聊着,转眼就到了韩睿泽在花云寨为裴奈安置的住处。
推开院门,院中的石凳上正坐着她意想不到的人。
裴奈惊中带喜,“你怎么来了?”
鞠连丞脸上却明显没有欣悦,仍旧寡淡,而且似乎因为依曦即将成为皇后的事,多了些愁容。
“寨民们说你住这,其他地方我待得不自在,来你这躲躲。”
裴奈摇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怎么没待在朝阳城,随军来花云寨了?”
“我父亲喊我来的,他说男子汉想要建功立业不可整日缩在府宅中。”鞠连丞解释道。
裴奈听笑了,“原来还是有人能治得了你。”
鞠连丞撇嘴,又看向裴奈身旁的韩睿泽,他应是认出了韩睿泽的身份,毕竟韩睿泽腰侧别着的珲洗鞭天下无人不识、无人不晓。
“这位是?”韩睿泽问道。
裴奈引见介绍道:“他是鞠言的儿子——鞠连丞,你们俩从前见过吗?”
韩睿泽摇头否认,“不曾。”
他已经而立,而鞠连丞才正处舞象之年,刚到了议亲的年纪。这十年韩睿泽又一直待在花云寨,二人不识也是正常。
韩睿泽将头转向裴奈,一挑眉,裴奈明白他的意思,他想问她为何会和鞠言的儿子玩到一起去。
“我这具身体来源于一个病重逝世的女孩,她叫唐明枝,是鞠夫人亲妹妹的女儿,也是鞠连丞的表妹。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暂住在鞠府。”裴奈补充道。
韩睿泽便明白了,听到第一句话,他就清楚鞠连丞已知晓裴奈的真实身份。
他对鞠连丞礼貌笑着邀请道:“有失远迎,我给裴奈备了午膳,很快会有人端过来,和我们一起用吧。”
鞠连丞没有推拒,随他们一起进屋,可入座后,目光仍落在韩睿泽脸上,忽地开口:“你和你哥哥很像。”
韩睿泽听此微微睁眼,似有些诧异。
裴奈急忙解释道:“连丞有过目不忘的异常天赋,所有声音、景象、气味、触感,只要他亲身经历过,便不会忘却,每一幕回想时都分毫不差地浮现在眼前。”
韩睿泽听完愣了几息,喃喃问他:“那你记忆里,我哥哥什么样?又做了什么呢?”
鞠连丞回想着,不费吹灰之力,往事便呈现在他脑海里,“他很好,为人爽朗,昂藏八尺且高风亮节。”
又继续说道:“他还提起过你,在都城的一个宴会上。宴会前几天你因为路见不平,不忍看良家妇女被恶霸当街欺凌,将那恶霸揍得骨断两处。那恶霸是太子少保的三儿子,太子少保一家找上门,事情闹得大。”
韩睿泽颔首,示意确有此事。
鞠连丞又道,“宴会上有人问他,‘令弟怎么没来?’他一举酒杯,笑说‘我将他撵回军营了,我这弟弟爱闯祸,确实不省心,给大家见笑了。’”
韩睿泽和裴奈都能想到韩睿岐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和神情。
“又有人道‘韩将军对令弟还是偏护着的,手足情深,令人艳羡啊。’你哥哥当时摆摆手,状似无奈,‘没法不管啊,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很小时父亲就不在了,我不管他谁管他?’”
韩睿岐的一颦一笑仿似出现在他们面前。
随后鞠连丞的一句话,让韩睿泽直接红了眼眶,“他状作无奈,可提起你时,脸上分明满是骄傲。”
房间里一片静寂,没人能够开口。
直到韩睿泽平息了情绪,如同调侃,“我父亲以身殉国时,我才一两岁大,我的鞭法,都是我哥教的,于我而言,他既是长兄,又像是父亲。我其实是他的负担,但他从未觉得。”
裴奈抚开眼角的泪,像是转移话题,好奇问道:“你把太子少保儿子给打了,你哥罚你了吗?”
韩睿泽摇头,“他知晓我动手的缘由,只怨了我一句‘索性要赔偿,不如直接对着下身踢,断两根骨头便宜那狗东西了。’”
裴奈笑了笑,泪滴又没止住地滑落。
她终是握拳,那么厉害的人,却因裴家军的叛徒而战死在赤山之战,“我们仇还没报完。”
韩睿泽先取了帕子,递给裴奈示意她擦擦脸颊上的眼泪,反问她:“拓跋霍你已替我杀了,你是说赤山之战的叛徒?”
裴奈点头,痛心疾首,“除了萧彬的出卖外,裴家军内部也有叛徒,能提前知晓郭伯父部署的人,怎么计也超不过二十个,我们必把他揪出来,郭伯父、韩大哥,还有数万的裴家军将士,这刻骨血仇,不得不报!”
韩睿泽看了看鞠连丞,有话要说,在无声问她是否能在外人面前讨论此事。
“连丞不是外人,他与鞠言一道,此事上我们立场一致,你说吧,没事。”裴奈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