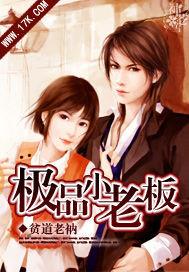456小说网>四合院之1947我来了 > 第148章 牵挂(第1页)
第148章 牵挂(第1页)
夏天的傍晚,杨婶坐在四合院门槛上,树影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晃来晃去。
手中的信笺被反复摩挲得发皱,杨志远的字迹工整得过分,“娘,这里山清水秀,每天都能吃上热乎饭。”
的句子旁,隐约有道歪斜的墨痕,像是握笔的手突然颤抖过。
她用拇指轻轻抚过那处,仿佛能触到儿子受伤的掌心。
随后杨婶揣着攒了半年的鸡蛋去供销社,非要换些云南白药。
“婶子,这药可金贵着呢。”
蔡全无为难地搓着手。
杨婶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对银镯子,那是她唯一的嫁妆:“就换这药!
我儿子在山里。。。。。。”
话音未落,眼眶里的泪水终于决堤。
“杨婶,喝碗绿豆汤降降火。”
徐慧真端着粗瓷碗走来,却见老人的手死死攥着信纸边缘,骨节泛白。
杨婶突然把信往她手里一塞:“慧真你识字多,快帮我瞧瞧,这训练时扭了腰几个字,是不是写得特别重?”
墨色在"
扭了腰"
三个字上晕开,像洇开的血渍。
深夜,杨婶的屋子还亮着油灯。
她戴着老花镜,就着昏黄的光将儿子的信平铺在炕桌上,用缝衣针小心翼翼地挑起信纸,仔细端详着。
背面果然有淡淡的血迹,就在"
一切都好"
的字样下方,蜿蜒成细小的溪流。
老人的嘴唇剧烈颤抖,却死死咬住,生怕哭声惊醒隔壁熟睡的承平承安。
徐慧真推开杨婶虚掩的房门时,正看见老人对着煤油灯,用绣花针挑开儿子来信的纸背,自打李天佑去了前线,她就时不时的带孩子回来住几天。
月光透过窗棂,在杨婶佝偻的背上投下蛛网似的影子,银发间夹杂的几缕灰丝,在灯影里微微颤动。
“杨婶,”
徐慧真的声音放得极轻,像怕惊飞了灯焰上的飞蛾,“您看这信纸上的血印子,像不像咱胡同口老槐树上的树胶?”
她挨着老人坐下,指尖轻轻抚过信笺背面那道蜿蜒的痕迹,“去年小石头爬树摔了,血蹭在作业本上,也是这么淡淡的红。”
杨婶的针突然掉在炕桌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徐慧真捡起针,从针线笸箩里翻出块褪色的红布,用剪刀细细剪出个小布人:“我听运输队的说,西南的山都长着会流血的树,杨志远说不定只是帮老乡砍树时蹭破了手。”
布人歪歪扭扭的脸上,她用墨点了两颗笑眼,“您瞧,这小人儿腰不疼,还能帮咱扛柴火呢。”
老人突然抓住她的手,指甲掐进她掌纹里:“慧真啊,我这心里头跟揣了秤砣似的。。。。。。”
话音未落,眼泪就砸在布人上,晕开两团深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