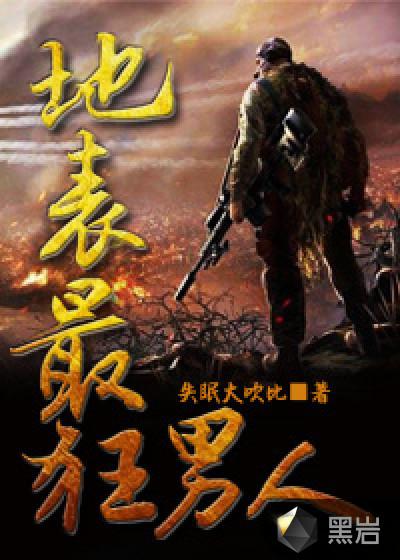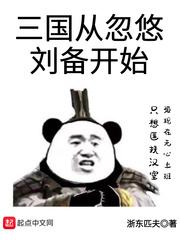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张志强马胜利吴铁军重生千禧年官场之路从片警开始 > 第259章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第1页)
第259章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第1页)
工地上的喧嚣,隔绝了山风的呼啸,却隔绝不了刘清明内心的冰冷。
他捏着那一沓薄薄的、泛黄的单据,指尖上传来的不是纸张的触感。
而是一种责任。
679。44元。
这个数字有多沉重?
他来云岭乡之后,特意了解过农民的收入状况。
东山村这种纯靠土地刨食的村子,一户人家一年的纯收入,能有五百块就算丰年了。
绝大多数,都徘徊在三四百块。
这意味着,他们辛劳一年,不但颗粒无收,反而要倒欠乡里两三百块。
农民收入单一,主要依赖卖粮或养殖,但提留需以现金缴纳,导致部分家庭被迫卖粮甚至负债。
提留统筹之外,农民还需承担“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如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等。
甚至出现“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的顺口溜。
韩志诚的供词中提到,乡干部用提留款抵顶吃喝账,导致14农户拒缴,他带人催缴的时候,农民质问“到底是给国家纳粮还是给干部吃喝纳粮”。
部分干部为镇压反抗,雇佣村霸、地痞协助征收,进一步损害政府形象。
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转嫁至农民,提留统筹成为基层重要财源。
但征收标准模糊,部分干部利用信息不对称加码收费。
农民通过上访、抛荒耕地等方式表达不满。
矛盾激化时,个别农民甚至采取自杀威胁或暴力对抗。
以上种种,就是当前“三农”问题中最大的一个。
身为一名党员干部,一个乡镇的领导,在这一刻,他天然地与身后的农民站在了对立面。
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收缴这些提留统筹。
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是上级考核他政绩的重要标准。
他该如何向甘宗亮解释?
说这些杂七杂八的收费,几年后就会被国家彻底取消?
他没有这个权力。他甚至无法正面回应甘宗亮那个充满期盼的请求。
“乡长……”甘宗亮看着他越来越沉的脸色,心里也跟着打鼓。
刘清明抬起头,将单据仔细叠好,收进自己的包里:“这事我知道了,单子先留在我这里。”
他能想什么办法?
带领村民致富,他有信心,但这需要时间。
可眼前的困境,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不能公然对抗政策,宣布免除这些费用。
没有这个权力,也干不出这种事情。
甘宗亮没再多问,转身去干活了。
刘清明一个人站在工地的边缘,看着远处热火朝天的景象,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力。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指尖触碰到一张硬质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