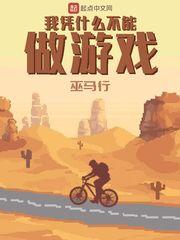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与敌为邻by > 第315章(第1页)
第315章(第1页)
>
江叶红摸着下巴,“确实啊,可是薛序能有什么把柄给岳东郎拿捏着。”
“喵呜——”岳东郎家院子里传出一声骇人的猫叫声,江叶红给吓了一跳,“大白天叫什么呢,怪吓人的。”
旁边邻居家的妇人又打开了大门,“烦死了,自从岳东郎不在家后野猫天天跑他家院子里乱叫,白天叫,晚上叫,吵死了。”
巫长宁,“自从岳东郎不在家后才开始的,从前没有是吗。”
妇人,“自然,我在这儿住五年了,哪里见过野猫天天这么叫的,过个年都不安生,吵死了。”
巫长宁朝江叶红递了个眼色,“踹门!”
江叶红唇角压出个弧度,一脚把门踹开了,院子里差不多七八只野猫,一见有人来四处逃窜,巫长宁见屋门敞开了一条缝,“要离家一段时间门都不关好的吗。”
江叶红,“大概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怕人偷。”
巫长宁哭笑不得,刚迈上台阶,令人作呕的恶臭扑面而来,房檐上的野猫发出凄厉的叫声,巫长宁蹙深了眉头,轻轻一推,门咯吱一声打开了,更为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巫长宁忍不住捂住口鼻后退一步。
江叶红上前一看,马上拉着巫长宁站远一些,扶着墙忍不住干呕,巫长宁也是头一次忍不住揉了揉鼻头,“先拿帕子捂着。”
江叶红摆摆手,“这……我回去叫人,这种事还是让老霍来吧。”
巫长宁摇摇头,“气味确实难闻,但我还能忍受,你先回去叫人。”
江叶红实在不忍巫长宁身上沾染这种味道,苦着一张脸,“要不,我进去吧。”
巫长宁,“好了,听我的,你去叫人,快去!”巫长宁把江叶红推走,用帕子掩住口鼻重新回到屋门前,深吸一口气,房檐上的野猫又凄厉的大叫一声,听得人头皮发麻。
巫长宁径直走向岳东郎的屋子,先把窗户打开散一散屋里的味道,巫长宁眉头锁紧地盯着地上的尸体。
美人灯5
巫长宁顿了一会儿,推门入屋,恶臭熏人,从尸体腐烂的程度上判断少说也有十天了,从过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三日了,最近几日天气转暖,尸体腐烂的更为严重。
尸体四肢被一指长的钉子钉在地上,钉子的尾端已经没入血肉里,喉咙处也插着根长钉,岳东郎的衣裳是素白长袍,肢体上的衣裳除了四肢位置别的地方很干净,不过有些野猫踩过留下的痕迹,他被钉在地面上的时候应该是完全没有反抗之力,地面上早已干涩发黑的血迹是下钉的时候溅出的。
巫长宁检查胸口位置,没有外伤,也没有打斗留下的淤伤,巫长宁强忍着干呕的冲动将岳东郎的头移开,后脑勺浑浊一片,恶臭熏人,巫长宁不适得合了下眼睛,继续查看,后脑勺指头大小的空洞,应该是长钉之类的尖锐器物留下的,从伤口处不难看出,应该是开了空洞后把人放在这儿的,然后任其流淌。
岳东郎脖子上的钉子嵌入得很深,不过巧妙地避开要害,脖子上的钉子非致命伤,那么只有脑后这一处致命伤了,四肢的出血量很大,加上脖子和后脑,上半身阴出的血比下半身要很多。
巫长宁发现岳东郎的右手还放着一杆画笔,笔尖上红色的绘料已经干了,笔是放在撑开的手掌上,右手五指完全被掰断,好生残忍的手段。为何要掰断岳东郎的右手五指后在他的掌心放一支笔。
左手手指并未折断,但是掌心放了盛有绘料的小碟,小碟里干了的红色绘料和笔尖上的是同一种。
巫长宁站起来走到门口,远看岳东郎的尸体像作画时候的姿态,故意把尸体摆成这个样子,有种出于报复的意味。
“阿宁——”江叶红带着六扇门的捕快赶来,进门一看岳东郎的尸体赶忙跑出去干呕,霍察嫌弃地翻了个白眼,“去去去,你们吐完了再进来。”
霍察放下工具箱,“阿若发现什么了?”
巫长宁靠在门框上,“四肢皆有伤但不致命,躯干之上未有任何伤痕,喉咙处的长钉虽深,也只是把人钉在了地上,巧妙的避开了要害,后脑处的孔洞应该是致命伤,凿穿头骨,任其流血而亡,初步判断只有脑后一处致命伤,左手持碟,右手执笔,尸体摆放的样子像画师在作画,而且岳东郎本身就是画师。”
霍察赞赏有加地大笑,“你说的没错,只有脑后一处致命伤,四肢上的钉子虽然可怖但只是外伤,而且他被钉在地上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巫长宁,“右手五指皆被掰断,又将画笔置于掌心,结合岳东郎画师的身份,把尸体弄成这个样子有种报复的意味。”
霍察掰开岳东郎的嘴,眉头一紧,“牙齿全部被打碎了塞在嘴里,他跟凶手是有血海深仇不成?”
巫长宁见尸体双唇紧闭,唇边也无伤痕暂时没有检查,不成想还有伤情,岳东郎死前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打碎牙齿活血吞……”
霍察,“或许有这种可能,从凶手行凶的手段上来看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唇边无伤痕,也无血迹,可见凶手清理过了。这是什么?”
霍察从岳东郎的鼻子里夹出几缕带血的棉絮,“鼻腔给棉花塞着,只有几缕是半塞,不是全塞,可见凶手恨毒了死者。”
江叶红完全不想靠近这扇门,挥手让巫长宁过来,“里面那具尸体真是岳东郎?”
巫长宁,“初步看应该是,不过还需人来确认,你去把邻里叫过来辨认一下。”
江叶红边走边干呕,过了一会儿叫过来几个男人,虽然尸体已经腐烂,面容还能确认,他们都指认尸体确实是岳东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