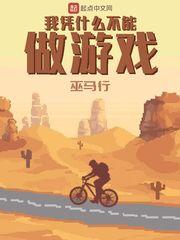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与敌为邻by > 第341章(第1页)
第341章(第1页)
>
萧流云摇摇头,“说得也是,听闻一些王公子弟以吸食此物为风尚,更别说民间,但是此物终归有害于身体,长此以往人就废了。”
江叶红叹气,“我去跟柳大人商议一下,让柳大人写折子呈奏陛下,就看陛下愿不愿意惩治这股不良之风。”
萧流云攥着拳头,“应该直接禀明裕王殿下,趁着整治藏灯之风连带着把这股萎靡之风一起收拾了。”
江叶红,“萧姑娘,还是需要直接上奏陛下,若是直接去找裕王,这是僭越。”
萧流云一怔,“楚捕头说得是,流云莽撞了。”
巫长宁,“萧姑娘,陆大人可是对孙远虑的美人灯颇有微词?”
萧流云,“是,这也算个人喜好,陆大人只是不满把美人灯捧得太高,从而贬低别的灯,听闻他曾在聚贤阁就此事写过一篇文章,不过遭到了美人灯拥护者的严词谴责。”
巫长宁越发感觉这背后有很多说不明道不白的事,“我们先去会一会这个林逸闲,萧姑娘今日请恕我们不能陪你了。”
萧流云笑笑,“办案要紧,我也要回史馆做事了。”
江叶红和巫长宁直奔崇明街,顾家医馆的旧案告破后这条街上多了些生气,不过大白天人还是见不到几个人,两人沿着空荡的街道直奔林逸闲的家,漆黑的木门,看还有几分怪异,江叶红上前敲了敲门,一会儿功夫门缓缓打开,开门的男人身量不高,很是纤瘦,麻色的长衣,衣摆沾满了青色的石灰,脸上也白一片黑一片的。
“刻碑还是做木雕,刻碑先选碑面用石,要刻什么字写清楚,做木雕也一样先选木材,要雕什么自己写清楚。”林逸闲说话的口气很冷漠,眼睛总是低垂着,从始至终都没看巫长宁和江叶红一眼。
江叶红心里嘀咕,就这态度生意能好才是见鬼了,江叶红拿出腰牌,“六扇门办案,你可是林逸闲?”
林逸闲将挽起的袖口撸下来,狠狠甩了甩袖口上的石灰,“是。”
江叶红挺不喜欢这人的态度,怎么说呢就是很欠,“你可认识岳东郎?”
林逸闲家的院子北侧放着三排未雕刻的石碑,石材还不一样,东边堆着的原木就显得极为杂乱无章,林逸闲拿过搭在椅背上沾满石灰的长布,对着刚打磨的石碑狠狠抽了抽两下,带起一阵灰尘,江叶红赶忙站远一点儿,“问你话呢?”
林逸闲将石碑上的灰尘抽干净,不紧不慢抬了下眼皮,“您都找上我了,自然也知道我和岳东郎是什么关系,至于我认不认识他还需多问吗?”
“你!”还真是刻薄,怪不得能和岳东郎那种人走到一起去,“岳东郎死了你可有听说?”
林逸闲将脚边的凿子丢进工具箱,“听说了。”
“听说了?”江叶红不由提高了声量,“你就没有一点儿……”
林逸闲站起来,拍拍袖口的灰,“哼,没有一点儿什么?我是该给他披麻戴孝还是守孝三年啊。”
不难听出林逸闲口气中的哀怨,“岳东郎这人,好的时候也是真好,坏的时候也是禽兽不如,我和他早断了,他是生是死都和我没有关系。”
江叶红,“我再问你,两年前的千灯展,笑忘书的木灯被谣传花钱雇人投签一事,可是你散布的谣言?”
林逸闲少有地抬起了眼帘看向二人,乌黑的眸子,近看了无生趣,透着一股恶意,“跟我有什么关系?”
江叶红深吸一口气接着问道,“但是田望说和你有些过节,而且谣言有可能是岳东郎传出去的。”
“哦……”林逸闲拿出一把较为细的凿子继续刻碑,“可能吧,我跟岳东郎抱怨过几句,兴许他是喝醉了,也可能是没管住自己的嘴胡说八道了。”
江叶红真来气了,“就因为这些莫须有的传言,田望的灯被千灯楼退了回来,还为此背上了弄虚作假的污名而丢了举人的身份,你就没有一丝愧疚?”
林逸闲冷笑,“愧疚?我为什么要愧疚啊,又不是我传的谣,官爷您要问责怎么也轮不到我,就算是岳东郎传得,也得需要证据,至于田望有没有弄虚作假,只有他自己知道,一盏平平无奇的木灯得签竟然比美人灯还多。”
林逸闲说话的声音很轻,有时候听不出语调,但是听着极为毒怨,尤其说到美人灯的时候,“那你是觉得田望的木灯不配和孙远虑的美人灯相提并论?”巫长宁突然发问。
林逸闲眯起眼睛打量了巫长宁几眼,不屑地轻哼,“自然是不配,田望算什么东西也配和孙远虑相提并论,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巫长宁,“有些东西不是配不配的问题,有人觉得好,自然也有人觉得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准则。”
林逸闲拿凿子的手顿了下,冷冷扫了巫长宁一眼,“哼,我一个刻碑的当然没资格评论,田望的事我不知道,你们不如招魂问问岳东郎,看看是不是他口无遮拦说出去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江叶红大怒。
林逸闲,“官爷好大的火气,我一个贱民能有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对官爷来说很重要吗?官爷要问的我也答了,不满意我也没办法,我这人说话就这样,您多担待。”
江叶红憋出一肚子火,“阿宁,我们走。”
巫长宁走到门前回头看了林逸闲一眼,刚好碰上林逸闲毒怨的目光,“你和岳东郎断了,什么时候断得?”
林逸闲垂下眼帘,吹了吹石碑上的灰,“很重要吗?”
巫长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