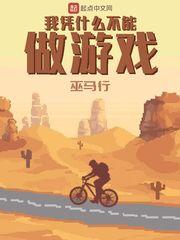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苏武牧羊的寓意是什么 > 四十(第2页)
四十(第2页)
常惠的心其实已经在胸腔内突突突地狂跳起来,但他还是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边干活,一边随口问道:“接走了吗?”
“哪能那么容易就被接走了呢。”巴登换了个坐姿,将身子正对着常惠,“你猜,我们的新单于是怎么对你们的使者说的?”
“怎么说的?”
“新单于谎称苏正使死了好些年了。”
周围安静极了,只有这两个人的对话在枯草塄坎间起起伏伏。
阳光将常惠干活的影子缩得很短很短,一不留神就到了脚下。空气中弥漫着枯草败叶以及牛羊粪的味道,整个原野都在短暂的暖阳的爱抚下,静谧得如同沉睡的婴儿。
哐哐哐,唯有常惠这里发出的响声很清亮地在草野里漫开。
有好长一段时间,常惠只埋头挖坑栽木桩,一句话也没说。
“怎么又不吭气了?”巴登感到寂寞无聊,又脸朝着常惠说道。
常惠就等着巴登的这句话呢。巴登的话音刚一落,常惠立即一脸高兴的样子,冲巴登眨了眨眼,说道:“就知道你巴登不是一般人,所以,你一定能够领我见一见汉朝来的使者了?”
“什么?这,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巴登瞪了瞪眼,有点结巴了,“你怎么光给我出大难题呀!”
“我知道你一定行!”常惠脸上显露出一副憨憨的笑意,连忙又是夸奖,又是竖起大拇指。看到巴登还在犹豫,他马上用贿赂对巴登展开攻势。
“你如果领我见了汉朝使节,我这个月的薪饷全归你,算是答谢,也算是为你给父亲买药尽一点力。”
“那行吧,但要等到晚上。”巴登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常惠兴奋得几乎要跳将而起。
阳光笑了,到处洒下喜人的光辉,空气也跟着欢喜万分。近处的鸟儿,一会儿冲向天空,一会儿扑进黄色的枯草丛中,远处的牛羊群与头顶的白云交相辉映。
常惠干活的劲头更足了,他一边挖坑栽桩,一边暗暗祈祷今晚神明保佑,能够让自己顺利见到来漠北的汉朝使节。
常惠使劲地干活,刨挖的土坑一个接一个连成了一长串,远远望去像人怀揣着的希望,等待着好时机的到来。
常惠挖啊挖,恨不能将太阳一就砍坠落了。时间是个怪物,当人想让它跑得快点时,它却慢慢腾腾,如同坡地里的牛,缓慢得令常惠心焦。
身后不远的地方突然闪出一只野兔,白茸茸的毛十分耀眼。尽管兔子机警地看着常惠和巴登,但它却忘记了它的天敌。一只在旁边一棵大树上等了好久的黑老鹰瞅准了机会,冷不丁飞扑而下逮了个正着,可怜的白兔一下子就在铁一般的鹰爪下被抓到了空中。
巴登看到常惠干得很卖力起劲,他那深有着游牧民族特色的四方大脸盘上,肉墩墩的鼻子向上皱了皱,笑了,对常惠说:“我又没赶着你催着你做活路,你那么拼命干什么?都干了好久了,还欢实得像小马驹一样。”
常惠甩一把汗水,有点气喘地回应巴登道:“怕你们的丁灵王卫律惩罚啊!”
“难道丁灵王长了一双千里眼不成,能够隔山看见兔出气?”巴登红红的高颧骨笑成了两朵花。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胡乱说着一些天南海北不着边际的话,说得时间都疲乏了,拽着太阳快快地往西边远远的大山背后滑去了。
夜色由草原的四面八方向这边聚拢过来,归圈的牛羊马在这个时间里嗅到了夜晚的特别气味,纷纷打着响鼻,咩咩咩、哞哞哞地叫唤,牧人即使不赶,它们也会向自己的圈里潮水一样涌去。
草原上的生灵自有草原的特征,它们啃食这里的青草长大,喝这里的清水成长,它们的血脉里同样传承着这一方水土的秉性,有着这方旷野的特色,成为游牧民鞭下不同的风情。
常惠跟着巴登,脚下划开正在铺展但还未彻底落下的暮色,向着来时的军营狱帐走去。
快分手时,常惠叮嘱巴登:“巴登,可别忘了咱俩今晚约定的事情。”
巴登咧嘴笑了,声音里明显裹上了草原夜晚的潮湿气:“忘不了,你放心。老交情了嘛,还有什么信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