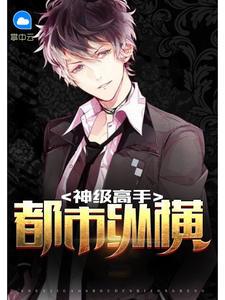456小说网>党家山庄山君 > 第二十九回 倡议建村塾 造福穷苦人(第1页)
第二十九回 倡议建村塾 造福穷苦人(第1页)
党进解囊救人的事迹使丰先生感到欣慰。因为这是他教出来的学生。
丰先生也想帮助穷人,他会在空余时间里教铁蛋念几句书,但铁蛋毕竟没有正式入学,这使他颇有感触。他心想,葱峪里这么多人家,值得办一所村塾或私塾,让这些可怜的孩子都能念书。于是,他就想向人们提出这个建议。
此时,张家有一位名叫张老三的人,领着他的孙子来山庄求学。他对党太爷说:“我家人老几辈都没有读书人,说难听点儿,都是睁眼瞎子。
我这小孙子人都夸他很聪明,但现在已十一岁了,还没有条件念书。能不能叫娃在你家书院就学,我愿多出点学费给你,求你给予关照。”
太爷难为情地说:“张老兄,你可叫我为难了。我家没有办私塾,只是请个教书先生而已。请先生不是为了办学赚钱,你给钱有什么用?我们的目的是让儿孙们求功名、奔仕途。你给我再多钱我都不敢收,所请的教师也不应允。再则,收了外边的学生,必然会分散先生的精力,影响我家孩子的成绩。我收了你一个,再来第二个、第三个怎么办?真对不起,请回去吧。”
张老三十分失望地走出了城门,碰见了党殿臣,也不由自主地说出了来意,这次说得更具体。他言道:“我们穷人家娃念书,不敢妄图做官求功名,只要能识几个字,会写会算就行了。他们最多能给人家店铺当个相公,混碗饭吃就满足了。”
党殿臣听了,心中不是滋味,但也无言以对,只好推辞,安慰老汉几句。
晚上闲坐时,丰先生提到办村塾的事。殿臣说:“我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不过这是村上的事,咱只能做个发起人,号召村上办学,为家乡做点好事,权当是积德行善。”两人一拍即合。
殿臣开始行动了,他首先找到本村的里正,说了自己的想法。里正当然赞成,但又提出了具体的困难,说道:“咱这穷山沟,谁愿意来这里任教?关键是请先生难。”两人陷入了沉思。
正说着,前几天去党家的张老三也来里正家串门。他听说请先生难,深思了一会,插言说:“请先生嘛,有一个人可以考虑,就是河西的郭荣身。他舅家在太和堡,城西有个大古庙,庙内办着个私塾。他从小就住在舅家,在那里念书,可能运气不好,连考了五次才过了县试。后来在同州府试,考一次落榜一次,到现在还是个县童生。他无力再考了,家里的钱,几乎让他花完了,就跟着税课司大使收税管账,听说也没挣下几个钱。我想把他请回来教教书,也许他愿意。”
里正听言拍手叫好,说道:“行,我看十有八九能行。他长时未回来,可叫谁去联系呀?”殿臣踊跃上前说:“我去试一试,你们等我的消息。”里正道:“凭你那举人的身份,你说句话,他不能不考虑。他即使有架子,也不敢在你面前摆。举人老爷请他,他应该感到荣幸。”
殿臣大笑,说道:“里正真会说笑,什么举人老爷的,我无一官半职,与平民百姓差不了多少。许多人要求到我家书院来,叫我十分为难,能办个村塾是对我的解脱,为了大家也是为了我。”里正道:“大人真谦虚。”屋内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殿臣和郭荣身也算是个熟人,他们曾经还坐在他门前的河边上聊过天。同是读书人,能说到一块儿去,所以他愿去联系。
恰好听人说郭荣身有事回家,殿臣不必下山,直接上他家联系。他大踏步走进郭家院子,一只小狗汪汪地叫着。听见狗叫,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走出堂屋。此人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温文尔雅。他拱手道:“幸会,幸会!党老爷光临寒舍,我有失远迎,快进屋叙话。”
宾主互让坐下,郭夫人拿烟沏茶。
殿臣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郭荣身谦言道:“晚生实在惭愧呀,山外一般坐馆的先生,最少都是秀才,我只是个县童生,还是别露面为好。”殿臣一笑,言道:“你谦虚了。没有考中秀才可能是运气不佳,能通过县试已称得起文人了,证明你已熟读‘四书’‘五经’,学问肯定是有的。再则咱山中多穷人,也不指望孩子考取什么功名,只要不当文盲就行了。这个标准你一定能达到。听说你给人家收税管账,薪水甚低,还不如在家教书,一方面花费少,挣的钱可全落下,另一方面还能侍奉年迈的父母,抽空还能干点农活。”说得荣身点了点头,但内心仍有疑虑。殿臣又说出了一套具体的实施办法后,他才同意回乡教书。
和郭荣身说妥后,里正便召集全峪的人家开会,讲了党殿臣的主张,大家热烈响应。殿臣还当众捐银五十两,作为建房之用。里正赞扬了他的义举和功德。
会上通过了如下决定:
一、聘请郭荣身为“葱峪村塾夫子”,长期任教。
二、每户每年摊粮五升,作为郭先生的最低报酬。
三、拜师的束脩礼、学费等,按社会上的常规进行。
四、在郭家的地面上修三间大房作为教屋。
五、全体动员,义务出工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