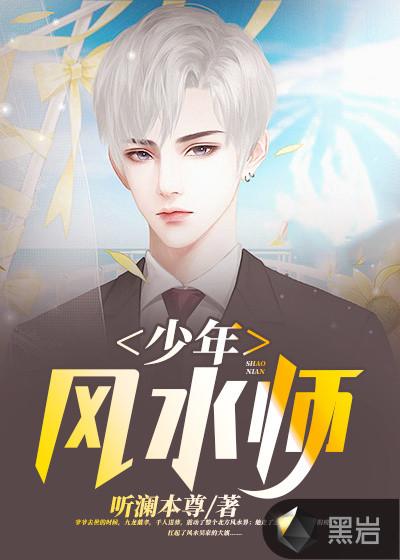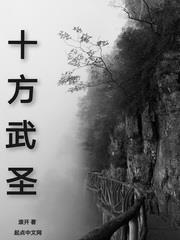456小说网>漫泉寺简介 > 02(第2页)
02(第2页)
过去,在电还没有普及时,人们照明用的是清油灯。试想,那样的夜晚是怎样的夜晚啊!肯定是漆黑无比,伸手不见五指——经常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讲,现在的夜晚不如过去的夜晚那么寂静、那么黑暗——可是,在仲秋的夜晚,明月当空高悬,银辉洒满四野,一条河水潺潺而流,河岸两边杨柳婆娑,附近荷塘中传来一阵阵的蛙鼓蛐鸣虫叫之声,漫步野外小径上,置身一个比平日亮堂的夜晚,欣赏着月色,听着水流声,这是何等美妙的一幅乡村秋夜图啊!沐浴在这么美的景色中,景不醉人人自醉啊!据说,当年杜甫从长安到蒲城探望妻儿,路过漫泉河休息时便创作了那首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诗中流芳百世的千古名句,大概也是感慨这样的美景与饥寒交迫的百姓生活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吧。
漫泉河之所以能够这样令人流连忘返,另外一个原因是这里曾经驻扎过一支英雄的部队。漫泉河谷两岸曾经是这支部队的营房、训练场和俱乐部,人们称这支部队为“漫泉河部队”。这支部队的官兵在漫泉河两岸驻扎了几年,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以后能不对这里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吗?何况这支英雄的部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参加过麻栗坡对越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以后这支部队的官兵不管走到哪里,漫泉河的名字始终会萦绕在他们的心田,许多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漫泉河那敦实的古石桥、蜿蜒的古河道,那记录着当年人水共融繁荣景象的出土石碑,那碧波荡漾、随风起舞的苇花、柳絮,无不提醒我们,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景和资源是十分宝贵和稀缺的,失去之后,就无可挽回,就会成为伤痛。我们一定要着眼未来,珍视现在,爱国家,爱家乡,爱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每一寸土地和胜景,用勤劳的双手,千方百计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2011年11月25日刊登于《渭南晚报》小狗哈哈
哈哈是一条狗的名,家里人都这样叫,我也就跟着叫了。
母亲和弟弟他们住在农村老家的时候,家里养了条狗,主要是为了看家护院。那条狗养了许多年,不知不觉已经显出老态。一个偶然的机会,弟弟从朋友处重新抱回来一条狮子狗,家里就同时养着两条狗,侄女便把那条小狮子狗唤作哈哈,并且投入了很大精力去喂养它,给它买奶粉,按时梳妆,定期洗澡,小狗就一天一天长大了。
哈哈在农村老家被养了两年多。我经常不在家,但是,逢年过节回去,哈哈总是像亲人似的迎接我,从来不曾对我高叫过一声。起初,我满以为是因为哈哈岁数小,还不懂得为主人履行看家护院的职责。后来渐渐发现,哈哈是认识我的,对来家里的其他陌生人它甚至会冲上去动嘴咬。
我感慨地说,这条小狗真通人性,它大概知道我是家里的主人。所以,我打心底里佩服起哈哈来,真聪明!
弟弟他们要把家搬出去,老家的院子也没有人再居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把哈哈送给舅舅家。就在弟弟他们将要离开老家的前几天,哈哈总是躲在没人的地方,不吃不喝,看样子很伤心。舅舅把哈哈接过去之后,怕它跑掉,就用绳子拴了一天,第二天它就认识了新家,再哪里也不去了。过了不久,我们回了一趟老家,顺路先去了舅舅家。哈哈看到我们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围着母亲、侄女和我前后左右地蹦跳,真有点“人来疯”的感觉。那次,我们从舅舅家领着哈哈一同回了趟老家。
不久,听别人说,舅舅把哈哈送人了。舅舅家本来就养着一条狗,哈哈去了之后,家里就有了两条狗,舅舅比较要好的一个朋友见到哈哈,就向舅舅讨要。尽管舅舅舍不得,但还是碍于情面把哈哈送给了那个朋友。
我听到这件事之后,心中还不由得滋生了些许抱怨,也不知道舅舅的这个朋友能不能把哈哈喂养好。在老家时,侄女可是隔三岔五要给哈哈洗澡的,哈哈也和我们建立起了比较深厚的感情。不是城里住房小的话,我一定会把哈哈带出来。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哈哈与我们分开已经快一年了,偶尔我也会想起哈哈,但是从来没有再提过有关哈哈的话题,毕竟舅舅已经把它送给了别人。这次,表弟办喜事,我们一家都回去贺喜。一进舅舅家门,哈哈也不知道从哪里就蹿了出来,围着我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蹦跳嬉闹,真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我非常感动,这么久了,哈哈还记得我们,还与我们这么亲近,看来狗确实是通人性的,难怪许多养宠物的人会和宠物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过去,我对那些养宠物的人持有偏见,这回通过与我们家哈哈相遇相识相分离的经历,我真被这条通人性的小狗折服了,它们有时候要比某些人更讲情义得多!
临走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哈哈又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给它招了招手,它就箭一般地扑了过来,我抚摸了一下它的头,抚摸了一遍它全身,它站在车门前一个劲地摆动尾巴。围观的人不知道谁说了句,是不是哈哈也要上车跟着走?但哈哈终究还是被留下了,车子慢慢启动后,哈哈又蹿到了车子的前方,跳动着,摇着尾巴,我再一次被哈哈感动了,它和我们多亲啊!
以后回去,还有个任务,就是要去探望哈哈,看看它生活得怎样,过得好不好。哈哈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牵挂,谁让它那么有情有义呢!我也暗暗地祝福哈哈健康活泼,好好活着。
2011年5月2日
烧炕
我是在北方农村长大的,土炕陪伴我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代。
过去,农村的房子基本都是土木结构的厦房,房子中盘的都是土炕,主要材料是胡基和泥基,也使用少量的砖块。胡基是人工加工的砌筑墙壁的较规则的黄土砌块。它是把黄土填在专用模具中用石夯夯打而成的,长40多厘米,宽30多厘米,厚六七厘米。过去农村盖房子,墙体基本上都是用胡基垒砌而成。泥基是为了盘土炕专门用麦草末和着泥巴制成的砌块,一般长60厘米,宽40厘米,薄厚也是六七厘米。它是把黄土和麦草碎末混合,加水和成黏稠状的泥巴,经过反复踩踏,使泥巴变得筋道,然后放进木模具中塑型,去掉模具后晾晒干即可。简单说,泥基就是铺就土炕炕板的组件。匠人盘炕时,用胡基做支腿,把泥基一个连着一个架在胡基上做炕板,除了下方的支腿,其他地方都是架空的,侧面留着炕门洞。
烧炕的时候,把柴火从炕门洞中塞进去,使其在里面燃烧,土炕就会慢慢变热。过去,农村人冬季取暖主要靠烧热炕,能生起炉子的家庭只是极少数。所以,冬季的农村,天黑前烧炕是丝毫马虎不得的事情,否则的话,漫漫长夜就会成为难眠之夜。热炕的特点是睡下之后,身子下面暖和,而被窝外面却冷飕飕的。一般情况下,人钻进被窝,手脚就不愿意再伸出来。
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平时回到家,除了割猪草、帮大人干农活和家务,冬季的黄昏就经常帮助大人烧炕。冬季农村的傍晚,烧炕是雷打不动的活儿,奶奶、妹妹、弟弟和我谁有空都会承担这个差事。每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烧炕,柴火燃烧释放的烟雾就会把整个村子笼罩,空气中总会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因为冬季要烧炕取暖,所以,农人在秋季就要把庄稼的秸秆拉回家,把麦衣、玉米芯、棉花壳等拾掇起来,晒干,储存好,以备冬季烧炕取暖用。用于烧炕的柴火主要有玉米秆、麦草和棉花秆,炆炕主要用的是柴火的碎末,爱睡热炕的农人烧完炕之后总喜欢再加上几把柴火碎末炆炕,以保证后半夜炕还热着。倘若遇到下雪天,储存的柴火上就会被罩上厚厚的积雪,勤快的人家就会及时收拾一些柴火放到屋内,以保证烧炕所需的柴火不被融化的雪水浸湿。倘若不提前拾掇点柴火,待柴火被雪水浸湿后,烧炕时,柴火就不容易燃烧,而且还会闷出许多黑烟,常常会呛得人睁不开眼、喘不出气,弄不好一个夜晚炕都热不了。
那时候,由于大人们要干田里的农活,散工都会在天黑之后,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烧炕的活都是由孩子们来承担。我每次烧炕,基本上要同时烧三个到四个,包括叔父、叔母的炕我都烧过许多次。邻居家有一个爷爷,腿脚不太灵便,喜欢睡热炕。他烧炕时,总是跪在炕洞口前,一撮一撮地把柴火往炕洞中塞填,平时甚至把儿子儿媳妇的炕都同时烧了。他的同龄人就调侃老人,笑话他当媳妇孝子,老人自嘲地答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放点账,等将来动弹不了的时候,还等着儿媳妇伺候呢!话里语外透露出些许无奈和苦涩。在农村,晚辈给长辈烧炕是天经地义的,而长辈反过来给晚辈烧炕,特别是给儿媳妇烧炕,在传统观念较重的农村就显得有点不太合情理。
据我观察,邻家爷爷之所以这样委屈自己,是因为他清楚,他的儿子老实、本分、木讷,儿子能娶个媳妇就得帮他守着,所以他们老两口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儿媳妇,即便是儿媳妇比照常理把事情做得过分些,他们也能忍气吞声,不与她计较。他们不愿意惹儿媳妇生气,担心会把儿子夹在中间为难,更担心滋生矛盾之后,会对儿子的婚姻造成伤害。那时,我们村子打光棍的男子多达十几个,有的甚至一家弟兄几个都讨不到媳妇。
娶回媳妇倘若再不花心思守着,那不是自寻烦恼吗?
最近几年,农民把房子基本上都翻修了一遍,土木结构的房子全部变成了砖混结构的楼板房。年轻人也像城里人一样,卧室不再盘炕,而改买席梦思床了。有些年龄大的人冬季睡惯了热炕,仍坚持在房子盘炕,不过现在盘炕使用的材料变成了楼板、砖和水泥沙子,再不用过去的胡基和泥基了,而且炕墙、炕沿上都贴着瓷砖。奶奶去世前,也从原来老房子的土炕上搬到了新房子的水泥楼板炕上,总算睡了一阵子具有现代气息的楼板热炕,奶奶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
土炕是一种记忆,冬季黄昏农村烧炕的烟雾缭绕也成了家乡的味道。
现在,家乡尽管保留下来的土炕越来越少,但是它荡漾在我心田中的滋味却历久弥香。土炕,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一种昔日生活的写照,更是一抹浓浓的乡愁!
2014年5月6日
乡愁
我是在农村出生的,随后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阶段。
农村曾经让我煎熬过,让我痛苦过,让我讨厌过。农村的日子苦,农村的灰尘大,农村的条件差,农民的收入低,我也像成千上万的农村孩子那样,曾经把“跳出农门”作为这辈子高于一切的梦想。
家乡那个地方的地下水是高氟水,人畜的生活用水无奈只能是它。饮用高氟水,最明显的特征是,从小孩起牙齿就发黄,有的甚至牙龈出血,我曾经就患过这种疾病。中老年之后,不是腰痛,就是腿疼,大多数人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看着别的地方的同龄人那雪白的牙齿,中老年之后腰板依然那么硬朗、腿脚依然那么麻利,我曾经深深地抱怨,我的家乡怎么会是这样,自己怎么会出生在自然条件如此差的地方。
家乡处在关中道卤阳湖的北侧,那里大概也是当年卤阳湖的湖底范围。家乡的黄土中,埋藏着大量大大小小的蜗牛壳。蜗牛喜欢阴暗潮湿的生活环境,寻觅腐烂植物为食。我推测,大概是由于地壳的运动,卤阳湖湖水渐渐退去,湖底暴露,以至于生长了大量植物,给蜗牛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才使这一带繁衍生长了那么多蜗牛。蜗牛死去后,尸体腐烂,壳就永远地留在了深厚的黄土层之中。
20世纪80年代,国家投入资金,解决高氟区居民的饮水问题,家乡才从洛河岸边引来自来水,使人畜的饮用水实现了根本性变化,从此才停用了祖祖辈辈不知饮用了多少代的高氟水。其实,从表面看,家乡的高氟水,清澈透明,无色无味,冬季从井口会冒出热气,夏季清冽甘甜,特别是在口渴难耐时,舀上一瓢凉水一股脑儿灌进肚子,真是既解馋止渴,又解乏降温。但是,这里的地下水中含有大量氟化合物,它对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利,长期饮用会造成氟中毒。
家乡的土地属于垆土地,经常利用地下水浇灌,土壤板结得比较厉害。引黄工程把黄河水送到家乡以后,浇灌庄稼大多使用黄河水,机井水基本成了辅助水源,这样一来,家乡的土壤也被改良了许多。过去,那些土地除了种庄稼,也再不适合其他经济作物的生长。最近几年,经过黄河水的反复浇灌,土壤比过去酥松了许多,品质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外地的客商纷纷来到家乡承包土地,栽种西瓜和大棚菜等经济作物,这种事情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家乡发生了变化,我对家乡的眷念也越来越深。但说句公道话,我并不是因为家乡饮用了自来水,土壤被黄河水改良了,所以才感到家乡可爱了、亲切了。其实,从灵魂深处讲,对家乡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毕竟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童年是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度过的,那里长眠着我祖辈三代亲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自然对土地就有着一种无以言状的亲切感,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踏上家乡的土地,我都会满怀激情和兴奋。那是一种从血液中、从心底涌出的对家乡那块土地的依恋和挚爱之情。
有空回到家乡,我总喜欢一个人去田野走一走、转一转,看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总是感到无比亲切,对它们也充满深厚情意。再回想一下当初离开家乡时所滋生的不良情绪,年少轻狂的缺点就显露无遗。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再比较,最适合恬淡生活的还是家乡,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更是家乡!
我爱家乡,更爱家乡的土地!城市的水泥钢筋楼房、卫生洁净的环境固然胜过农村,但是,能从心底撩拨起我爱恋之情的却始终是家乡的那一方土地。我天生是农民的儿子,近30年的城市生活不仅没有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城里人,反倒使自己对家乡更加依恋、更加眷念,归根结底,是因为那一方土地始终释放着无尽的魅力,那里已经成为自己这辈子永远魂牵梦萦的地方!
201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