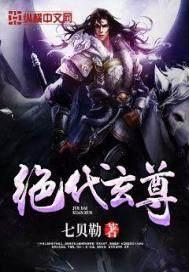456小说网>漫泉寺简介 > 第五辑 亲情绵长(第1页)
第五辑 亲情绵长(第1页)
我的爷辈们
我家爷爷辈有弟兄四个,爷爷为大,有父亲和叔父两个儿子。二爷有三个女儿,小女自幼被送了人。三爷早年随他舅舅家的表哥去兰州闯荡,因病殇到了外头。四爷经爷爷的朋友介绍到铁路上谋到了差事,跟着铁路从兰州一直到乌鲁木齐,后来扎根在那里,膝下有两女一子,儿子十多岁时不幸夭折。
我出生后,在长辈的循循善诱下,逐渐对家里的亲人有了印象,他们的身份也由此确定下来:太奶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二姑、叔父等。太奶奶80多岁高龄,患老年病,行动不便,总躺在床上,奶奶每天把太奶奶抱出抱进、喂吃喂喝,炕前檐下服侍。爷爷每天干完生产队的活,晚上和太奶奶住在一起,挪体翻身、端屎端尿。太奶奶年岁高,经常说胡话,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趣谈。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吃饭的闲人多,爷爷、父亲、母亲累死累活地在地里干,二姑没黑没白地在学校干,为的是多挣工分、多分粮。奶奶守在家,八口人的饭要做,衣服要缝补,我和太奶奶需要人照顾,寸步都不能离。就这,太奶奶还从炕上摔下来过一次。那是奶奶去上茅房,嘱咐我守护着太奶奶。太奶奶在土炕上爬动,眨眼的工夫就摔到了地上,我吓得又哭又叫。奶奶闻声后跑回来,把太奶奶抱回炕上,心疼得几天都没个笑脸。
慢慢地,我觉得我家好像与别人家有点不一样,爷爷管家很凶,家里人都怕他,在村上闻名。每天早上爷爷总是早早起来,叫醒一家人,或下自留地干活,或给猪圈拉土,或背上笼去拾粪,有时候连我和六七岁的妹妹也不放过,让每人带上个棒槌跟着大人们去自留地打土坷垃。我和妹妹蹲在地里一边慢慢向前挪动一边挥动臂膀敲打。那时,我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能被大人呵护着不用去田里干活。再就是,爷爷、奶奶似乎与别人家的爷爷奶奶不大一样,他们之间从来不说一句话,奶奶有什么事总是让父亲他们给爷爷传话,爷爷给奶奶钱或者别的什么,也是经过我们孩子转手。我的心里很疑惑,爷爷奶奶怎么这样呢?
随着一天天长大,我慢慢知晓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家本来是爷爷弟兄几个共同的大家庭,从来没有分过家。因为很早就没了爷爷,我所谓的“爷爷”其实是爷爷的弟弟——二爷。因为我们孙子辈一出生就这样叫,二爷在我们的眼里便是“爷爷”。姑姑们本来也应该唤作堂姑,我们家,奶奶为嫂,我眼中的“爷爷”为叔,父亲和姑姑们是堂兄妹。就这样,叔嫂二人“爷爷”主外,奶奶主内,他们拉扯着父亲、堂姑们,艰难地打发着苦焦的日子。之所以“爷爷”奶奶彼此不说话,我想大概还是受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传统的影响吧,特别是嫂子和小叔子之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母亲给我讲了许多老辈人的心酸往事。
旧社会,爷爷在岳庙街给人打工经营店铺,找机会给四爷在外面找了份工作。因为家里有收入,日子还可以,加之有太爷爷这个“天”罩着,二爷不担沉,基本上是“二七不离河口、三八不离庙上”。意思是,只要三河口和西岳庙逢集,二爷就会每集必去。
后来,爷爷突然患了不好的病,经治疗无效后不长时间便去世了。临终前,他拉着二爷的手说,他把父亲托付给二爷了。那时,奶奶31岁,父亲只有12岁,叔父还没有出生。祸不单行的是,爷爷去世不到一年,二奶生了三堂姑后不久,也突然病倒了。二爷把二奶带到省城去看病,几个月后,二奶也不幸去世了。二奶的后事才刚刚处理完,四奶又病倒了,二爷只能强忍着悲痛,又举债带上四奶再去省城治病,所幸的是四奶最终痊愈而归。三起祸事,前前后后拉扯两年多时间,对于一个普通农家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时,二爷把不满半岁的小女儿送人了。
1959年,三门峡库区移民,老爷爷举家迁移到蒲城定居,三四年后也去世了,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生存的担子就全部落到了二爷身上。自此,二爷变得沉默寡言了,也更凶了,他咬紧牙关支撑着。庆幸的是,外面干事的四爷也尽最大努力帮衬二爷,他除了自己吃饭穿衣,基本把剩余的工资都花给了这个大家庭,一大家人才能艰难地向前过着日子。
经过接二连三的打击,我家的日子就非常困难。可是,二爷没有倒下来,没有气馁,只是走路比过去更快了,起床更早了,睡觉更晚了。他拉扯着子侄们拼死拼活地挣生产队的工分,细心耕作自家那点自留地,帮助太奶奶、奶奶搞点家庭副业……其间的苦楚,别人真是很难理解。一句话,是二爷以超常的毅力撑起了这个家。后来,太奶奶去世了,我的弟弟妹妹出生了,二堂姑出嫁了,叔父也复员回来成了家,我们家才一分为二,叔父赡养了奶奶,父亲赡养了二爷。
我没有见过爷爷,在我的记忆中,二爷就是“爷爷”,他对这个家的付出、对子女的关爱,如果用语言来形容的话真就显得太过苍白了!还有四爷,他尽管没有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但也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这个家。几十年来,他总是坚持给家里寄钱,接济这个家,直到侄子们都成家立业。现在逢年过节,他每次总要寄回两份同样的礼金,一份给大嫂,一份给二哥,陆陆续续地,他还给“爷爷”、奶奶置办了棺木……以至于我第一次去乌鲁木齐时,从他居住的两居室中,无论如何也丝毫感觉不到四爷是个干了30多年铁路工作的老同志;还有奶奶,作为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为了这个家和她的子女,牺牲的何止是一辈子的幸福啊!从她身上看到的应该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平凡影子啊!
爷辈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是什么,人应该怎样去对待亲情。今后的岁月,我们只有用心去体会他们用行动实践过的亲情观和是非标准,继承他们团结协作的好家风,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不断地把日子往好了过,才称得上是爷辈们的好儿孙!
载1998年11月30日《澄合矿工报》高祖在潼关城中有生意
在老潼关城里,我们先祖留下了生活的足迹。高祖父曾经在那里经营着一个车轴铺子,有三间临街门面房,主要是为出入潼关的马车更换车轴。那时候出入潼关,关内关外的车轴不一样长,留下的车辙宽窄也有差别,车轮如果不合辙,就无法行驶。所以,出入潼关的车辆都需要在关口前更换车轴。当时的车轴是木质的,一般使用枣木或者榆木等硬木制作,因之高祖的木匠生意还比较红火。
高祖育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二、老四都随着他在潼关城中经营车轴铺子,老三在华阴县(今华阴市)三河口附近的三阳乡三阳村卫家城子务农。高祖经营车轴铺子赚了不少钱,从潼关城中把可观的钱财捎回老家交给高祖母管理,高祖母把钱到处藏匿,墙壁的夹缝中、屋内的顶棚上、脚地的洞穴中,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圪里都是她藏钱的地方。高祖母对藏匿银钱的地方守口如瓶,直到她去世时,也没有告诉过子女。高祖母匿藏的有银圆、铜钱和国民政府的法币等,许多法币到后来被找到时已经变成了废纸。
高祖去世后,儿女们分家另过,兄弟四人就开始独立过各自的日子。
据老辈人讲,高祖父四个儿子中,老大小名叫崇,老二叫明,老三叫喜,老四叫什么已经打问不出来了。潼关城中的生意交给长子崇料理,二子明和四子也返回农村老家度日。那时候,在华阴县三阳乡三阳村卫家城子,老二有个独院,是一间半宽的庄基;老三、老四和老大住在一个院子,是个三间宽的庄基。这两院庄基相邻,都是面南背北,一间半庄基在西,三间庄基在东。
高祖在潼关城中的铺子经营到第三代的时候,高祖的嫡孙、长子崇的大儿子卫科生,也就是我的堂爷爷接手了这个车轴铺子。卫科生堂爷爷有个爱好,特别喜欢听书,在书场听得不尽兴时,常常把说书先生请到铺子中说专场,什么《三侠五义》《说岳全传》《忠义水浒传》之类的,他想听什么,说书先生就说什么,以至于把潼关城中的街坊门面卖掉用来支付说书先生的薪酬。在车轴生意不景气的时候,他还做过宰牛的屠夫,开过豆腐坊。卫科生堂爷爷在潼关城中曾经娶了媳妇,他的脾气比较古怪,成天有事没事就殴打媳妇,女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他。家里的长辈训斥卫科生堂爷爷,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今天走个穿红的,明天还会来个穿绿的。卫科生堂爷爷以后再也没有续弦,也没有留下子嗣,新中国成立后成了生产队的五保户,去世之后他的坟墓几乎成为荒冢。
卫科生堂爷爷自小在潼关城中长大,身上沾染了许多坏习气,算是个缺乏责任心的人。按理说,上辈人把生意交由他经管,他就有义务把生意传承下去,不发扬光大也罢,最起码应该守护好祖上的基业。再者,他曾经娶妻,但脾气古怪,对妻子不是打就是骂,逼得人家出走,最终连一儿半女也没能留下。他的弟弟因为参加永丰战役阵亡,弟媳带着三个侄子艰难度日,他竟然把弟媳和三个侄子卖与他人。本来大侄子成人后是要返回来顶门立户,并为他养老送终的,可是侄子回来一次,他打骂一次,导致侄子终究没能返回老卫家,直到他去世都未再谋面。
卫科生堂爷爷从潼关城中回到华阴老家,已经是解放后的事情。1959年,三门峡库区移民,老潼关城被搬迁,华阴老家也要迁移,卫科生堂爷爷按照国家移民政策随家族一同迁移到蒲城县贾曲乡南贾曲村一队生活。
当初,他没有经营好祖上留下的生意,也没有循着普通人的路子留下子嗣,更没有担负起失去父亲的侄子的抚养责任,还把他们卖与他人。由此不难看出,高祖的基业是败在嫡孙卫科生堂爷爷手中的。难怪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一代的基业最终是需要后辈来继承的,如果后辈人缺乏责任心,那前人未竟的事业必将半途而废。
卫科生和爷爷是堂兄弟。爷爷辈的弟兄们有个共同特点,性格都比较内向,弟兄们之间也不太沟通交流,各人却都非常有主见。迁移之后,爷爷为一个姑姑找了个婆家,因为这家人不是华阴迁移来的新社员(移民),而是当地的老户,为此,当对象春节前来拜年的时候,姑姑领着她对象去看望伯父卫科生,他显得异常生气,竟然把姑姑对象带的糕点之类的礼物从屋里扔了出来。这件事情很伤爷爷的面子,老弟兄俩从此便有了心结,姑姑的那桩婚事也泡了汤。
此后,爷爷与他堂哥卫科生的关系属于那种不即不离的状态。爷爷不喜欢说话,但总是暗中照顾堂兄。爷爷曾经为生产队务菜,每每有点稀罕菜,就想方设法给堂兄留一点。有一年秋季,爷爷为堂兄卫科生留下点西红柿,不料有个邻居家来了客人,想做顿变样饭,爷爷便把留下的西红柿让人家临时应了急。为这事,卫科生堂爷爷不离现场就和爷爷翻了脸。爷爷面对着这个蛮不讲理的堂兄,真是深不得浅不得,关系始终保持得不温不火。在卫科生堂爷爷去世后,爷爷和其他堂兄弟们悉心地把他安葬了。
我们的先祖曾经在潼关城中风光过一阵子,后来基业败落在卫科生堂爷爷手中,大概也是上天注定的。富不过三代是句俗语,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繁衍传承的基本规律。今天说道卫科生堂爷爷,因为他是高祖父的血脉。虽然他是个缺乏责任心的男人,人生也相当失败,但毕竟逝者为尊。
之所以把这些往事抖搂出来,主要目的是让后辈们记住这个先辈,并以他的人生为教训,防止再有后人重蹈覆辙。
2014年2月13日
爷爷,我不想让您走
天,阴沉沉的;雨,如丝如缕。
戊寅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这天,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爷爷走了,走得是那样从容。爷爷临终前给父亲、叔父做了交代,是关于如何过好日子的话;对堂姑们做了交代,是如何尊重兄长、扮演好相夫教子贤内助角色的话;对我们弟兄做了交代,是如何搞好团结、尊老爱幼的话。
爷爷疼爱我们。爷爷对于我们总是严肃多于和颜悦色,但爷爷的一举一动却都倾注着浓厚的爱意。
爷爷弟兄四个,三爷外出闯荡时殇了;四爷在外地工作,家属子女全在老家。爷爷兄弟几个没有分家,共同维持着一个大家庭。在1960年前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爷爷的大哥、妻子和父亲因病相继去世,老辈人中挑重担的只剩下爷爷一个,其他的就是太奶奶、奶奶和四奶奶,还有我们子侄们等六个孩子。从此,爷爷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
爷爷的担子重,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二奶奶去世后,爷爷没有续弦,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爷爷过日子很细,因为家里本来就穷,再加上祸不单行的那几年经济透支,劳力少、孩子多,日子就更难过。爷爷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天明觉,每天总是早早起来干活。那时候,生产队打铃出工,清早等铃声敲响上工时,爷爷肯定已捡拾了一笼粪,或者已领着父亲、堂姑们给猪圈拉了几车土。
爷爷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对子侄看起来很严厉,实际上他心里牵挂着每一个孩子,对哪一个都像亲生的一样。历经千辛万苦,使子侄们娶的娶、嫁的嫁,总算都有了完整像样的家。他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孙子辈身上,今天操心这个冷,明天操心那个热,这个定了亲,又牵挂那个还没嫁。他把自己捡拾破烂的收入和别人给的零花钱攒起来,从来都舍不得花,哪个需要接济就给哪个。他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子孙过不下去。平日里,他不固定待在一个地方,总是这个子女处走走,那个孙子处看看,不然就不放心,就睡不好觉。见了面,瞅上一眼,住上一宿,可以啥话也不说,就又踏上了新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