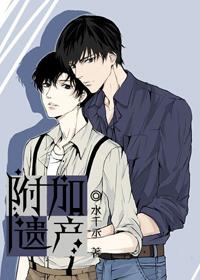456小说网>冰山笔记郭永清是谁 > 边地知青(第6页)
边地知青(第6页)
六
塔什库尔干县城东头街口是一个大下坡,坡下面拥挤着一片小土屋。下坡右拐,在一个小巷子里穿来穿去,走到尽头,一个大的栅栏门里,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场里拴着几头正在吃干草的干瘦的奶牛。院子的一角有三四间土屋。周红推开其中一间的门扇,探头进去叫了一声:“哥。”
屋子不大,屋内光线昏暗。屋子的一角有一张简易木床,床头边是一张三斗桌。泥墙上一方小小的墙洞用三根树棍隔了,蒙上塑料薄膜,算是窗户。光线就从那个墙洞里透进来。
一个年纪二十五六的年轻人头发老长,戴一顶旧军帽,穿一身蓝色红卫服,坐在桌子旁默默地抽烟。他个子不高,抬起头来,脸上灰蒙蒙的,额头上有明显的抬头纹。
他明显认识张勇。
周红介绍我:“哥,这是我们老乡。”
他的哥哥木讷地挪一挪身子,招呼我坐。在烟盒里给我摸了一支香烟。
他给我们把烟点燃,自己抽一口烟,若有所思。
“我家在褒河那里,离褒河很近。”他自己介绍自己,“我本来在家种地,在家种地也好好的。”他把烟徐徐地吐出。看起来,他很少和人交流,他希望倾诉。“可是,他们说只要到这里来就算知青,就可以解决城镇户口。我想,也行吧,先解决了,再想办法转回去。”
我心想:这谈何容易!
他果然又吐一口浓烟,说:“你肯定想,把户口再转回老家谈何容易。是的,我也想了,这简直是做梦。”
他又深深地吸一口烟:“走一步是一步吧。”
他的脸暗沉沉的,一副毫无希望的表情。
“我这就算是工作了,我这就是上班。”
我说:“你们就那几头奶牛吗?我怎么看不到别的奶牛?”
“四头,这个奶牛场就四头奶牛。一个场长,下边就我一个职工。这就是一个单位。你想想,这是牧区呀,家家户户又有牛又有羊,家家户户都产牛奶、羊奶,县城里的汉人屈指可数,就算他们天天喝奶,这几头牛也够了。我其实是没有什么事可做。”
他一副毫无希望的表情看我:“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回不去了。”
张勇说:“那你咋办?”
“你们当几年兵就回去了,我呢,在这里熬吧。”他咽一口唾沫。
从他那里出来,我的心情有一点沉重,作为一个曾经的知青,我们当年离开家时,不管怎么说还是生机勃勃。而这个周红的哥哥,有一点颓唐了。
我们和周红在巷子口分手,他回县城去,我们朝南顺大路返回团部。
七
几天后,我离开团部返回哨卡。我乘坐的是一辆援助巴基斯坦的大卡车,司机是一个甘肃籍的退役老兵。他在边防团招待所过夜,我去找他,求他把我捎到卡拉其古,然后,我在那里等待去明铁盖的便车。
我们的车走得很早,路过第二边防营菜地小屋时,天刚蒙蒙亮,我自然无法和小林他们告别。
隔着河,我又看见了对面的白房子。
司机开着车在驾驶室里和我聊天。
他说:“其实,你们有送菜的车上山啊,你怎么不坐?”
我说:“送菜的车有跟车的人,我们的司务长也在车上,这样我就只能爬大厢。坐你的车,我可以坐驾驶室啊。”
他问我,当兵前干什么,我说:“插队知青。”
司机说,他在这条路上跑了十几年了。他是军区汽车团的,集体转业,被派去支援巴基斯坦。
“兄弟,这条路我跑得太熟了。所有援巴的司机以前都是军人,只要是军人在路边挡我们的车搭便车,司机没有不停的。坐我的车,你不要客气啊!”他的这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汽车开出去五十多公里,路过一个叫达布达尔的地方。这是雪山峡口处的一片谷地,有牧场,有牧民的村庄。村庄房屋稀少,一律是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地散布在公路边。
司机突然把车停下,说要找水喝。他领我走进路边的一个院子,这院子有一排房子。司机说:这是达布达尔公社“革委会”。
一个汉族干部接待我们。他三十来岁光景,小平头,高个子,强壮结实。他一开口,我听出是南方口音。
司机说:“主任,搞点水喝。今天这位小兄弟也是知青。”
看样子,司机和他很熟。
原来,他是这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是从上海到帕米尔插队的,算我的前辈了。
他带我们到他的宿舍。半间小屋,陈设简陋。他端出一个煤油炉子,用一个搪瓷缸子给我们烧水喝。
“我是上海人,出来快十年了。”他自我介绍,“是被‘三结合’结合进班子的。”也许是这里的汉族人太少了,和我初次相见,说话就毫无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