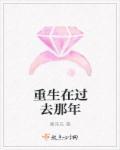456小说网>大秦历史的书籍 > 第三章 能臣悍将(第3页)
第三章 能臣悍将(第3页)
精辟的宏观之论,行之有效的操作之法,使秦王政为之感叹,他被尉缭的才气征服了。他感谢上天赐给了他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
尉缭之计,对于秦国来说,可以称作“金钱连横”,通过培养和收买东方六国诸侯重臣,破坏六国合力攻秦。后来的事实证明,尉缭之计的确发挥了极大作用。
尉缭作为军事战略家,不仅有出色的谋略,而且还有观人的本
领。秦王政“衣服饮食与缭同”,而尉缭却认为:“秦王这个人,高鼻子,长眼睛,挚鸟胸脯,豺狼之声。这种人缺乏恩惠,心如虎狼,俭约时容易谦卑,得志了就会吃人。我是布衣百姓,但秦王见到我往往低声下气。如果秦王真的得志于天下,天下人就都成为他的奴虏了。不能与他长期相处。”
在封建社会,议论帝王的相貌是犯忌的。但为了留住尉缭,秦王政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土:秦王政接见尉缭时,身穿同尉缭一样的衣服;秦王的饮食也和尉缭一样。召见尉缭时,秦王政常常迎出门外。一时秦王政身上的帝王架子没了,骄横之气也不见了。然而,正是这种异常的举动却把尉缭给吓跑了!尽管秦王政是真诚的。
封建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僭越就是大逆不道,而大逆不道者,轻则要坐牢,重则要杀头。
秦王政的谦恭有些过分,过分的谦恭必有悖礼仪,有悖礼仪的行为使人产生怀疑,怀疑其人的不良动机。所以说尉缭有些害怕了,最终他还是选择离开。
当秦王政知道尉缭跑了之后,他怎能甘心对自己如此重要之人将他抛弃!秦王政急了,立即下令,派出快骑,追回尉缭!
尚未逃出秦国的尉缭又被迫了回来,被追回的尉缭心怀畏惧,然而,秦王政却既往不咎,他仍旧以礼相待,又以强制相留,并正式任命尉缭为国尉。
在社稷与个人荣辱间,秦王政遵循了吕不韦的“贵公去私、任贤使能”的道理。
由于秦王政不计前嫌,追回尉缭,仍以重任相托的真诚打动了尉缭,致使尉缭尽心竭力地效忠于秦王政,成为秦王政智囊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尉缭的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他和李斯一样,成了秦王政的股肱之臣,参与秦王室的最高决策。
秦王政当时所面对的形势是燕在北方,魏在南面,再与最南方的楚国联合,然后还与东方的齐国建立巩固的关系,再把近秦而贫弱的韩国连在一起结成合纵,组成一个由北向南的战线对抗强秦,秦国是很难快速取胜的。
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的胜利。秦国的战争总战略日益完善,概括起来说,就是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先灭韩、赵、魏三国,再攻两翼,最后操兵东进,灭掉齐国,完成华夏的统一。所以,尉缭子的战略思想对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尉缭自始至终参加了大秦王朝的统一战争,他不愧为这场统一战争中总战略的设计师!
世界历史大事记
斯巴达国王克利奥蒙尼三世(公元前237—222年)利用对外战争得胜,军队在握的有利时机,用暴力推行改革,重分土地。这一改革对其他城邦发生了影响,阿卡亚同盟中的大奴隶主惊慌失措,竟然联合马其顿扼杀了克利奥蒙尼的改革。
延伸阅读
尉缭不但在军事、情报、政治方面是个怪才,而且还是最早运用影武者战术之人。
公元前218年,当时的韩国贵族后裔张良为了报亡国之恨,专程从朝鲜之沧海君处请得一大力士准备暗杀秦始皇。但是因尉缭给始皇帝建立了相当完备的警卫体系,每次始皇帝出巡都会有多辆始皇帝的替身副车,使得张良暗杀的风险大增。终于张良选择了一处始皇帝要走的必经之地一个名叫博浪沙的地方埋伏,张良令朝鲜力士暗怀大铁锥隐于道旁,等到始皇帝一出现便用铁锥重击之。但是因为副车跟皇帝主车一模一样,由于无法准确分辨始皇帝在哪辆车内,朝鲜力士的暗杀以失败告终,力士因为体型高大很快被捕处死。而体型相对瘦小的张良却因为其不起眼的身材躲过了一劫,复仇失败后的张良便投靠下邳的刘邦。此影武者马车乃尉缭之杰作。
5.顿弱之谋
时间公元前236年
人物顿弱
公元前236年,秦军在前线正与诸侯酣战,眼看着各国诸侯已经衰弱,但他们仍要作最后挣扎,并且伺机合纵抗秦,尤其是韩、魏、赵三国居于诸侯七国中央之地,是秦东进的主要障碍。且燕园与赵国相临,若此四国合纵抗秦,必会对秦构成重大威胁。为了离间四国合纵,秦王嬴政忧心忡忡。这时,有一位叫顿弱的人出现了。
顿弱并非是秦国人,而是由其他国家入秦的游说之士,其身份相当于宾客,与秦王政不存在着君臣的关系。
秦王政闻知顿弱的大名,想要召见他,同他讨论天下大势,便派使者向顿弱转致这一意图。顿弱得知后,请使者向秦王政转达说:“臣客居秦国,按理相见时不能参拜秦王。秦王如能允许臣相见时不行参拜之礼,臣可以奉召晋见;如果不允许,那么,臣就不敢前往晋见了。”
使者一字不漏地向秦王转达了顿弱的回话,秦王政觉得此人虽然有点奇怪,但闻知出语不凡,揣想其人必有奇谋妙计,故意出此难题来试探寡人是否诚心招贤纳谏。想到这里。奏王便向使者说:“你转告顿弱先主。寡人答应他相见时不行参拜之礼的要求:
使者转告顿弱,顿弱便前往宫中见秦王:
“天下有一些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也有一些无其实却有其名的人;还有一些无其名且无其实的人,大王您知道吗?”赢政果然对此大感兴趣,他很干脆地回答:“不知道。”顿弱解释说: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便是商人。商人不种田种菜,但家中却囤积谷米,所以说商人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是农民,农民虽有生产粮食的名声,但家中却没有积粟,所以说农夫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人;无其名又无其实者是大王您啊!您虽登上了王位,拥有万乘车马、天下财富,却不能供养父亲,得不到孝子之称,自然也无孝子之实,所以,大王便是既无其名也无其实的人。
听到这里,赢政勃然大怒,顿弱明明是在挖苦自己。但怒言未发,只听顿弱又说:“山东有六个诸侯国,以大王的威力不能征服他们,可是却把威风撒在母后头上,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取啊!”顿弱这里所说的母后之事,是指嬴政亲政后因母亲有私宠行为而被他赶出宫的事情。
顿弱此时是在有意地刺激赢政,看看嬴政的耐心如何,而嬴政也经受了下士的考验。对于顿弱的考问,他听了虽然生气,但还是忍住了,并转过话题问顿弱说:“山东的六个诸侯国该怎样兼并呢?”
顿弱竟以赢政母后这样耻辱的事情和敏感的话题来刺激嬴政,无异于揭他的伤疤。依赢政对母后淫乱后宫之事的敏感程度,他早就要暴跳如雷了。然而,为了听到统一六国的良策,赢政宁愿受辱,这种克制力不可谓之不大。
顿弱见赢政未恼,便将话切入了正题,他献策说:“六国之中韩国所处的位置,好比天下的咽喉,而魏国所处的位置,好比天下的胸腹。大王可以给我万金,让我去韩、魏游说活动,收买韩、魏两国所信任的王戚贵臣,让他们为秦做事。秦若在他们国家有了内应,那么取两国就易如反掌。而韩、魏到手,天下也就会成为王的天下了。”
顿弱的话正合他的心意,赢政听了心里当然暗自高兴,但他却故意对顿弱说国贫,难以拿出万金来。而顿弱便又向嬴政讲了利害关系,他说:“天下不会这样容易就被取得,诸侯国之间不是合纵,就是连横。若连横成功,诸侯就得听命于秦,秦就能成就帝业;而若合纵成功,诸侯就会联合抗秦,并且听命于楚王。秦若能成就帝业,天下何止万金来供养大王;而楚如果成为天下之王,即使大王有万金之富,恐怕也不属于您了。”
顿弱说完,赢政大喜,他非常赞同顿弱的话,便采用顿弱的计谋,赐给他万金做资本,让他到东边游说韩、魏。不久,顿弱便实现了行间目的,收买了韩、魏将相效力于秦。接着顿弱又北上游说赵、燕,用金钱收买人心,使燕顺眼于秦,让赵悼襄王废弃名将廉颇,还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等人,陷害了名将李牧,将秦东进的大绊脚石搬掉。
顿弱接下来还到了齐国,让齐王向秦朝拜,迫使韩、魏、赵、燕四国服从于秦。
世界历史大事记
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前287~前212),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出生于西西里岛(Sicilia)的叙拉古(Syracuse)(今意大利锡拉库萨)。他出生于贵族,与叙拉古的赫农王有亲戚关系,家庭十分富有。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学识渊博,为人谦逊。他十一岁时,借助与王室的关系,被送到古希腊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城,跟随欧几里得的学生埃拉托塞和卡农学习,他以后和亚历山大的学者保持紧密联系,因此他算是亚历山大学派的成员。
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尼罗河口,是当时文化贸易的中心之一。这里有雄伟的博物馆、图书馆,而且人才荟萃,被世人誉为“智慧之都”。阿基米德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了许多年,曾跟很多学者密切交往。他在学习期间对数学、力学和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学习天文学时,发明了用水利推动的星球仪,并用它模拟太阳、行星和月亮的运行及表演日食和月食现象。为解决用尼罗河水灌溉土地的难题,他发明了圆筒状的螺旋扬水器,后人称它为“阿基米德螺旋”。
公元前240年,阿基米德回叙拉古,当了赫农王的顾问,帮助国王解决生产实践、军事技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