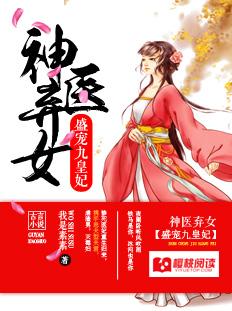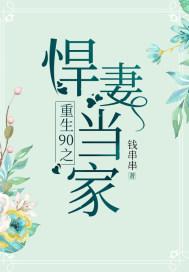456小说网>可怕的广东人作者是谁 > 第五章 重商爱商富甲天下(第2页)
第五章 重商爱商富甲天下(第2页)
1827年l0月,67岁的梁经国以年老多病为由,呈报粤海关以其子粱纶枢接办行务,天宝行进入经官二世时代。梁经国则于1837年去世。
为了重振天宝行,1828年(清道光八年),梁纶枢捐输河南修河费银95万两,但困境并没有解除。1839年2月,天宝行欠饷银近2l万两,占所有行商欠饷银总数的50%,清廷限令一年内缴清欠饷。虽多方筹措,但一年后仍欠饷7万多两,天宝行面临破产危险。此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已响,梁纶枢捐输海疆2万两,天宝行遂化险为夷,得以继续运行。
正如李嘉诚说:“毅力是一种心态,毅力不是一种生活。真正有毅力的人清楚自己人生的目标,且愿意承担责任,有颗坚强、非凡的又充满希望的心,知道什么是原则、事实与正义,有极大的勇气和谨慎。”在某种程度上说,成功靠的就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而这种毅力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3。依托海洋,盐业发家
广东是一个海洋大省,拥有全国最漫长的海岸线。至少从秦汉开始,广东就开辟了自徐闻、台浦、番禺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庞大的船队通过茫茫大海建立了联系着亚、非、欧的国际性商道。早在宋代,广州就被人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靠海吃海”的理念已成为广东沿海民众谋生的最重要途径。清初曾在广东做过地方官的蓝鼎元曾说,广东等地“人稠地狭”,田地根本不够耕种,要解决温饱问题,只能向海洋发展,以致出现“望海谋生十居五六”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广东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通过海洋来解决生计问题的。
北京路高第街内有一小巷叫许地,里面住着名门望族的许氏家族。许家的发达,也是从无到有一步步走的。清初,许氏家族的第一代从粤东澄海迁来广州时,十分穷困。第二代的许拜庭不仅成了广州一大盐商,富甲一方,而且繁衍了一个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许氏望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一位叫许永名(颖园)的30岁的潮汕汉子,不甘于乡间的寂寞。离开了粤东澄海沟南乡,来到了广州府,经营小本生意。
约莫过了十年,到了40岁上下的许永名手上有了一些积蓄。以一个壮年的血肉之躯,客居他乡,渐渐感到有些难耐的寂寞,遂萌起了在广州娶一门亲事的念头。
他将自己的心事对一位朋友说了,这个朋友很同情他的处境,托一个媒人为他介绍了一位姓黄人家的女儿。这位祖籍番禺的黄姓人家,主人名叫黄童贵,是一个穷儒。黄家排行第三的黄姑娘那一年才17岁。
乾隆三十六年(1771),许永名与黄姑娘正式成亲,一切按照番禺当地的婚姻风俗办事。老夫少妻,婚后感情融洽。男主外,女主内,婚后第二年,黄姑娘生下长子许拜庭,后来又诞下两个儿子。十多年过去,许永名突然患病不治。永名死后,黄氏带着3个儿子回到永名的老家,以为有遗产可以养大孩儿。岂料到了沟南乡才知道永名原来在家乡已有发妻。黄氏不甘作妾,便拖着3个孩子回到广州。一家4口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好心的舅父带着年仅13岁的许拜庭,将他交托给姓董的盐商,到盐店当童工。由于他勤劳能干,成为得力的店员,老板便派他出海购盐。老父的早逝,寡母的含屈,这一切使许拜庭还在弱冠之年,便懂得如何精细、周到地照顾母亲与家庭。那种为含辛茹苦的母亲争一口气的决心,那种中国人总想要光耀门庭和出人头地的欲望,时时刻刻驱策、激励和支配着他。
一次,拜庭受店主指派,出海购盐,同行的有另两家盐商共三条货船。然而,在三条货船满载食盐,返回广州途中,一场暴风袭来。风暴之可怕令人肝胆俱裂,拜庭知道此时进也死退也死,他大声咆哮:“伙计们,别无生路了,只此一搏!”他激励众人,冒死航行,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广州。据史料记载,这场特大的风暴,令伶仃洋一带的商船民船损失惨重,溺毙人口近2万。
三条船有了三种不同的命运,一条沉没,一条迷失方向,只有许拜庭不惧风暴沉着指挥的那条船能乘风破浪,死命逃出飓风的虎口,奇迹一般抵达广州的码头。不但东家本人,就连周边的商家,特别是与他结伴同行的两条盐船所属的两家商号,都被深深震动了。一时之间,人人争说姓董的盐商命好、运好,雇了像许拜庭这样一个遇事沉着、有心计、有远见、且“福星高照”的伙计,直把姓董的盐商说得喜笑颜开。
大风甫定,广州市面百业顿显萧条,特别是食盐供应短缺,闹得人心惶惶。姓董的盐商几乎做着独家生意,获利甚巨,深为盐业界同行所羡慕和妒忌。因而,商家目光集中到名噪一时的许拜庭身上。除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忠、勇、仁、义”外,他能“逢凶化吉”,还有“吉星高照”,因而带起主家生意兴隆的故事,撩拨着多少渴望发财致富、又难得人才的商家的心。于是,同业中一种秘密筹划在悄悄进行:有的大商号派人与许拜庭暗商,愿意给高工资雇用;有的则愿意斥资与他合伙开铺。
然而许拜庭面对种种诱惑不为所动,为报董盐商的栽培之恩,他始终忠心耿耿,“忠臣不事二主”。姓董的盐商也越发赏识他,并赠与许拜庭股份与之合作,继续经营盐业。后来,许拜庭终于独立出来,与弟弟许赓荣一起经营盐业,生意像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
也是生逢其时,当时清朝政府为了打消盐商的疑虑,解决商销纳课困难,于是实行招商政策,给予盐商以种种优惠。当时的盐课收入,成为除了田赋之外每年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成为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之一。而每年交纳盐课“正供”的盐商们,则属于与朝廷有着密切关系的、享有特权的商人集团。他们获得经营销售食盐的专利权,赚取高额的利润。不少盐商积累的资金往往数十万两以至数百万两之多,形成巨大的商业资本。
许拜庭就是在清朝政府这种一切为盐业生产、销售开路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之下,得以迅速地崛起于广州盐业界,并成为其中佼佼者的。
海洋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广东人重商轻农的反传统的观念,一部分沿海的广东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特的商人群体。广东商帮的主体就是由沿海的广州帮和潮州帮组成,所以人们又称广东商帮为海帮,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4。农业商化,财源滚滚
广东人大部分生活在沿海流域,人稠地狭的矛盾十分突出。但广东人与生俱来的商品意识使之克服了地域限制,广东人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走农业商化的道路。
广东台山市海宴镇的田野上,到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剑兰,其中有美艳的花蕾欲开,就如绿毡上点缀着花朵,令人陶醉。剑兰花,有特别欣赏价值。人见爱不释手。因此,订购此花的客商频频上门。
南头管理区陈浓发、陈浓沛、陈浓委兄弟三人,是种剑兰花的专业户,他们介绍道,剑兰是耐寒耐热作物,一年四季可以种植,春种可收花和种子,秋植可收花头,卖给别人种。目前他们种植51亩,品种有十多个:荷兰黄、日本黄、发毛红、西施??他们自产自销,在广州设立“陈青花场联络点”,服务一条龙,产品远销上海、南京、兰州、昆明等十多个城市,甚至出口香港、澳门。元旦、春节、清明等季节最为畅销。他们说,1993种植收花的剑兰21亩,收头的30亩,因遭强寒露风破坏、半造(8—12月)仍获纯利收
入21.5万多元。1994年,他们也种植同样的面积,因气候比往年好,剑兰生产旺盛,收入大大超过1993年。
五村管理区朱国文,夫妻俩于1993年种4。6亩,纯收入2万多元,1994年扩大面积种植到8亩,年收入达6万多元。
“种植剑兰花,财源通到家”,海宴镇的农户见到这是一项“三高”的农业,因此纷纷种植,现已发展到那马、安和、东溪、北头、在阁、估村等十多个管理区。1994年全镇种植面积已达1500亩,成为该镇一项可观的收入。
近年来,湛江雷州市流沙村在家家户户养珠的基础上,引进技术精心加工成珍珠工艺品,年加工珍珠已近3吨,年产值达4000多万元。他们的珍珠产品走出国门,远销到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年创汇近700万美元,成为闻名遐迩的珍珠村。
珍珠市场的活跃,促进了珍珠养殖和加工业的发展。如今,有900多户人家的流沙村,已从过去的单纯养珠卖珠,走向精加工的立体发展珍珠的新路。
他们算了一笔帐,0。5公斤珍珠售价5000多元,而加工成珍珠项链等工艺品,却可卖到15000元,价格提高2倍。以前要把珍珠拿到广州才能加工成项链,现在全部在本地加工,加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兴起。除工艺厂外,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加工作坊。他们将珍珠加工成项链、手链和耳环等高级装饰品,销往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养珠专业户尹国荣,提高珍珠质量后,自己加工的珍珠直接打进国际市场。
1994年7月,他们每月付15万元的高薪雇请了日本一名专家到他家当珍珠漂光技术员。在日本专家的指导下,加工的产品90%达到出口水平。仅两个月时间,尹国荣一家加工珍珠达300公斤,外销珍珠项链一万多条,为国家创汇80万美元。
养珠专业户尹大,投资60多万元,办起一间珍珠氨基酸厂,利用珍珠层
粉研制成珍珠氨基酸(即珍珠液),每年可产氨基酸5吨,产值100万元。现在,这里不少人靠养珠或加工珍珠致富,成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
元的富户。
近年来,湛江雷州市流沙村在家家户户养珠的基础上,引进技术精心加工成珍珠工艺品,年加工珍珠已近3吨,年产值达4000多万元。他们的珍珠产品走出国门,远销到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年创汇近700万美元,成为闻名遐迩的珍珠村。
珍珠市场的活跃,促进了珍珠养殖和加工业的发展。如今,有900多户人家的流沙村,已从过去的单纯养珠卖珠,走向精加工的立体发展珍珠的新路。
他们算了一笔帐,0。5公斤珍珠售价5000多元,而加工成珍珠项链等工艺品,却可卖到15000元,价格提高2倍。以前要把珍珠拿到广州才能加工成项链,现在全部在本地加工,加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兴起。除工艺厂外,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加工作坊。他们将珍珠加工成项链、手链和耳环等高级装饰品,销往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养珠专业户尹国荣,提高珍珠质量后,自己加工的珍珠直接打进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