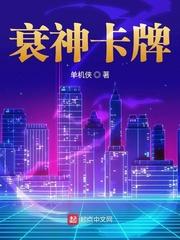456小说网>历史的魔法师 > 大宋王朝 传奇时代风云变幻(第6页)
大宋王朝 传奇时代风云变幻(第6页)
赵昺做皇帝以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炎二年(1277),福州终于被攻陷,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蒲寿庚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诸宗室及士大夫,南宋流亡小朝廷逃往广东。端宗准备逃到雷州,不料遇到台风,帝舟倾覆,端宗差点溺死并因此得病。
左丞相陈宜中建议带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并自己前往占城,最后逃到暹罗(今泰国)并死在那里。端宗死后,他7岁的弟弟卫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以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今属广东)却失败,于是在陆上已无立足之地,因此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皇帝的老师)张世杰护卫着赵昺逃到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上),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
不久,在广东和江西二省抗元的文天祥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元将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生擒,在陆地的抗元势力终于覆灭。
祥兴二年(1279),张弘范大举进攻赵昺朝廷。双方兵力对比为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仅有战船500艘,这时只到达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余万,两军在海上对阵。但是宋军没有大陆的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大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
宋军纵然能打败一次两次的进攻,可是在大海之上后勤断绝,后援也无,失败是必然的。宋军有强大的海军,却不实行流动作战,反而将千多艘船只以“连环船”的办法用大绳索一字形连贯在海湾内,并立起楼棚如城堞,并且安排赵昺的“龙舟”放在军队中间。这时宋军中有人建议认为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向西方的撤退路线。
张世杰为防止士兵逃亡,否决建议,并下令尽焚陆地上的宫殿、房屋和据点。
元军以大军猛攻,可是宋军防御严密,元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载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宋船。可是宋船上均涂满了泥,并用长木防御元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给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水道断绝,无淡水可用,士兵们吃干粮只能饮用海水,多呕吐肚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三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辞拒绝。
二月六日,张弘范发起总攻,第二天,张弘范将军队分成四部,乘着潮水正面进攻,同时元军南北夹攻,宋师大败,元军一路打到宋军中央。这时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和苏刘义带领余部十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
赵昺的船在军队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元军又杀至,43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已经受尽屈辱,陛下不可再受俘虏之辱了。”言毕背起9岁的赵昺,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和大臣亦相继跳海自杀,宋军民十余万投水殉国。
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以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昺的死讯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几天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以图再战。满心悲凉的张世杰却叹息说:“此时此刻,还用避风吗?我为大宋江山已经尽了全力,一位皇帝去世,我再立一位,现在新皇帝又死,这是天要亡我大宋吧。”不久风浪越来越大,座船倾覆,张世杰溺于海上,这位抗元名将饮恨于大海之中,宋朝正式灭亡。
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
——宋太祖与宋钦宗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陈桥兵变”的方式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成为五代更迭的最后一幕,由此可见武人干政的一斑。他怕后世仿效,施行一系列控制国家军队的政策,使得北宋一代积贫积弱。但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纷争,成为了一代雄主,与汉高祖、唐太宗并驾齐驱,也是一个历史伟人。与宋太祖相比,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真是相差甚远。宋钦宗实际在位仅一年多,却走马灯似地拜罢了二十六名宰执大臣,其用人的教训值得我们今人汲取。
开国之君小档案
身份北宋开国皇帝
姓名赵匡胤
在位时间公元960年~976年
特长骑射
嗜好踢球
最大敌人辽国耶律氏
继位者宋太宗赵匡义
谥号太祖
开国因素后周的准备、军事独立
用人得失
赵匡胤能夺取政权,统一全国,依靠了一大批智能之士和能征惯战的勇将。他和历史上建立王朝的其他开国之君一样,有一套驾驭群臣的权术。
(1)笼络人心。
大将韩令坤英勇善战,是赵匡胤的心腹。韩令坤与赵匡胤从年轻时起就是一对要好的赌徒。慕容延钊是赵匡胤的密友。当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时,慕容延钊任殿前副都点检,二人配合得很好。陈桥兵变时,韩令坤官居镇安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侯,正受后周之命在北方巡边,手握重兵。慕容延钊官居镇宁军节度、殿前副都点检,率重兵驻守真定(今河北正定)。这些人表示效忠新朝,这就稳定了大局。赵匡胤即帝位之后,每遣使劳问,对慕容延钊“犹以兄呼之”,可见其笼络之术。
宋太祖时常向大臣表示要共享安乐。王审琦不能饮酒。有一次宴会,宋太祖向天祝愿说:“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与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宋太祖对王审琦说:“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宋史·王审琦传》)。王审琦深受感动,果然连饮十杯不醉。以后,他赔侍宋太祖宴饮,总能喝大杯酒,而平时在家却一滴酒都不能沾。这是宋太祖动之以情,在心理作用下产生的奇效。这件事说明宋太祖以人情世故温暖臣下,这种用人术比威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2)以优容宽厚代替严诛。
宋太祖对功臣很忌惮,但他不是用诛功臣的办法来立威,而是以宽柔的办法成其意。例如王全斌取蜀立有大功,但他掠夺民家子女玉帛等不法事被人告发,论罪当大辟,宋太祖下诏优容,只给降职处分。几年以后,宋太祖把王全斌召来侍奉,一同郊祭,礼毕,重新任命王全斌为武宁军节度使,并对他说:“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宋史·王全斌传》)。还赏赐王全斌银器一万两,帛万匹,钱一千万。宋太祖这样处置王全斌,既严了法度,抑制了功臣,又不伤臣下的感情,让群臣宿将从这里看到出路,只要忠于朝廷,贪污受贿算不了什么。当然,宋太祖的做法,以优容宽厚代严诛,对于稳定当时的政治是有好处的,应当称道。
(3)择善而从。
宋太祖善驭群臣,也不是完全出于权术,他能倾听臣下意见,择善而从,所以,能够使君臣欢洽。例如,剑南刚平定的时候,禁军校吕翰聚集众人反叛,一时声势很大,当时有人建议尽诛叛军家属妻小。宋太祖很狐疑,他去征求李崇矩的看法。李崇矩说:“叛亡之徒,固当孥戮,然案籍合诛者万余人。”(《宋史·李崇矩传》)。宋太祖于是采纳了李崇矩的意见,下令赦免叛军家属无罪。这个消息一传开,叛军纷纷反正,不久吕翰就兵众散尽而亡了。
(4)容人之量。
赵匡胤很有容人的肚量,并且重视人才,曾经制定了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的祖训。赵匡胤表现出了一个帝王应有的自信和大度。王著原是后周臣子,一次,在赵匡胤召开的宴席上喝醉了酒,突然思念其故主,当众喧哗,群臣大惊。赵匡胤也是后周臣子出身,毫不怪罪,只是命人将他扶出去休息。王著却不肯出去,在屏风后面大声痛哭,被左右硬是搀扶出去。第二天,就有人上奏,要求对王著严惩,赵匡胤没有理会。他说王著只是喝醉了,世宗时候,我就和他同朝为臣,熟悉他的脾气,他一个书呆子,哭哭故主也没什么,由他去吧,最后也没有追究此事。
(5)用贤不用谄。
治政惟用人,用人须选贤。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具体实行起来,却并不这么简单。俗话说:人心隔肚皮,识人费思量。试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讲和就是识人之难。
事实上,用人比识人更难。因为人都有表象和本质的一面,大多矫作伪饰,真性情平常很难暴露出来,故而人贤奸与否,必先识之而后方能用之。自古以来,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分贤愚、辩臧否,选才而用之。如果能知人善任,则事业有成;如果不辩奸贤,枉徇私情,随意而用,势必导致事业失败。在这方面,宋太祖赵匡胤可谓一个智者,他坚持“用贤不用谄”,这独到而高妙的用人方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