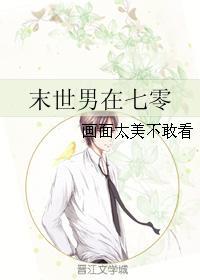456小说网>大隋帝国风云猛子 > 第二部分承上启下的大隋盛世第一章 隋文帝的文治武功(第2页)
第二部分承上启下的大隋盛世第一章 隋文帝的文治武功(第2页)
北魏灭亡后,北齐、北周分别继续实行均田制。
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下令:每个成年男子给露田80亩,妇女给40亩。奴婢比照良人给田。耕牛一头给田60亩,限止4牛。另外每个男丁给永业田20亩。永业田不还给国家,此外的田地都按规定退还。同时还规定了给田奴婢的数额:亲王300人,嗣王200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100人,七品以上官80人,八品以下官至庶人60人。这个均田制度,显然对官僚富人有利。高官不说,仅以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为例,如果他有60个奴婢,4头耕牛,就可以分到3840亩土地。所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在北齐,“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正说明北齐均田制是多么不彻底。
1-4隋唐饰品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规定:已娶妻者,给田140亩,未娶者给田100亩。另外,10口以上人家给宅田5亩,9口以下给宅田4亩,5口以下给宅田3亩。18岁成丁受田,64岁年老还田。但由于关中地区地少人多,有资料表明,当时普遍存在受田不足额的现象。
杨坚登帝即位后,立即重新颁布了均田法。规定男丁受露田、永业田皆遵北齐之制,园宅3口人给1亩,奴婢则5口人给1亩。官吏受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多者100顷,少者40亩。此外又给职分田,一品官给田5顷,以下每品减少50亩,至九品为l顷。外官也给职分田。此外还有公廨田,以充公用。开皇十二年(592年),在统一南北3年后,杨坚又派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把均田制在全国推行。当然,不能指望隋文帝的均田与前代有什么本质区别,杨坚实行均田,同样是照顾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杨坚实行均田,在当时至少起了两个作用:第一,均田令关于受田数额的规定,是对诸色人等占田的最高限额,这种限额对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多少有些限制作用。第二,杨坚所行的均田与赋税紧密结合。
北周的租调相当重,均田户每户纳调麻10斤;田租因户受田140亩,纳粟也增至5斛。如前所述,均田户尽管规定给田140亩,但实际给田往往不足额,而田租并不因为授田数额不足而有所削减。杨坚所行均田规定,均田户交租粟3斛,并明文规定未受地者不课租调。农民的租调负担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减轻。
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杨坚又下令实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办法。
“大索貌阅”
北魏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的同时,又颁行“五家设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的所谓“三长制度”。三长的职责除了推行均田、功课农桑、催督租课外,另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建立户籍,检查户口。很显然,户籍制度如不健全,国家的均田和征收赋役都是难以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隋文帝的均田诏令中,首先便谈到“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可见,隋文帝是把建立新的三长制度作为推行均田法令的前提条件的。而“相检察”的含义,除了推行均田和征收赋役之外,建立户籍、检括户口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实上,设置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可谓是“四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如不设置三长。由何人代表国家在乡里来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同样,如不建立和检括户口,均田和征赋又怎会有着落?可见,检括户口是推行均田和征调赋役的前提条件。
对于隋文帝来说,重视检括户口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与隋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自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地豪强地主的势力一直很强大。在豪强地主势力之下,很多依附农民即所谓“荫庇”农民是不在国家编制的户籍之中的,封建国家政权也无法向这些荫庇户征调赋役,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调蒙受重大的损失。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因而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已是势在必行。
1-5隋朝陶瓷青釉虎子
《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对于隋初这一形势有概括的论述: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弊,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泯。奉公蒙轻减之征。杜佑原注解释说: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通典》中的上述一段文字,深刻地揭示了大量农民荫庇于豪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西魏丧乱周齐分据的历史条件下,暴君污吏将繁重的赋役负担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农民不堪承受,才不得不依附于豪室,求得荫庇,以图活命。在法制紊乱败坏的年代,这种大批农民荫庇于豪强的情况,呈现出愈发严重的趋势。高颎于隋文帝建国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他目睹这一弊端的流行和严重危害,为此而建立“输籍法”。于是,对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从法律上逐一作出详细的规定,地方官吏不得在法规之外再征调任何其他赋役,使农民所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的数额,比过去大为减轻。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农民知道充当豪强的佃家,虽然可以逃避军家的赋役.但收获物的一多半却被豪强剥夺去了;而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却可以从国家所减轻的赋役负担下得到较多的实惠。两相对比之下,正如杜佑所解释的那样,在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轻税之法”下,原先荫庇于豪强的“浮客”,全部都自行脱离豪强,甘愿重归于国家的编户齐民。杜佑所说的“隋代之盛,实由于斯”,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书记载表明,《通典·食货典》所概括隋初面临户口隐漏情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例如北齐时,“阳翟一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户至数万,籍多无妻”。迨至隋初,“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同上)问题既然如此严重,隋文帝决定利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通过“三长”即保长、阎正和族正(在畿外为保长、里正和党长)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户口工作。于是,“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同上)隋文帝“大索貌阅”即大规模地检察户口的诏令,以其十分坚决而得力的姿态和措施,责令基层组织中的“三长”检察户口;检察过后仍发现有“户口不实者”,具体负责检户口的“三长”要处以流放远方边地的刑罚。与此同时,又特设负责受理揭发检举隐瞒户口的专门机构,以清查隐瞒户口的现象。再次,凡属于堂兄弟以下的,一律令其分家,另立户籍,以防止隐瞒户口现象的发生。可见,隋文帝检察户口的诏令,是坚决而得力的。
《隋书·食货志》又记载:“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即输籍法),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输籍法,从实际出发,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把每个农户应当负担的赋役数额以簿籍的方式确定下来,使农户免受贪官污吏的额外勒索,又使国家征调的赋役得以如数地征收上来。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收到了“自是奸无所容”的效果。
开皇初年所实行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效果十分显著,共检出443000丁,计1641500口。据《隋书·令狐熙传》记载,令狐熙任沧州1(治所在今河北沧县)刺史,在沧州大索貌阅,检出1万户荫庇于豪强的“浮客”。使之成为编入国家户籍的编户齐民。
检括户口的结果,隋朝的户口数增加得很快。据《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杜佑注说:“后周静帝末授隋祥,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干九百三十二。”《隋书。地理志》又载,隋文帝平定江南后,“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隋炀帝即位后,随着平定林邑、平定吐谷浑以后州I郡的增加,已达到“户八百九十万七干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干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以上户口和垦田数字。并非完全可靠,但隋朝户口数的迅速增加,则是不容否认为事实。
检括户口使许多逃亡灰民从豪强地主的荫庇下摆脱出来,这不仅使国家赋税收入大为增加,也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发展,仓储激增
隋朝的农业是在南北朝时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农具。据北魏贾思勰所著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的记载,当时的农具已有20余种,其中有不少农具在此前的史籍中是不见记载的。《齐民要术》对当时农业科技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均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瓜果等品种空前增多。此外,牛耕的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和设施的大量兴建等等,标志着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隋王朝建立后,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的推行,检括户口工作的开展,为隋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隋王朝存在的时间短,有关隋朝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形,史书记载甚少。可以想见的是,农业生产力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在隋初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之下,使得隋朝的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则是合乎逻辑的。就现有资料来看,最能说明隋朝农业经济发展的,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人口的增加和粮食产量的激增。而国家的广设仓窖和粮食储备的空前增加,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隋朝农业经济的发展。
1-6隋朝发明的水利筒车
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隋王朝建立后,调入京师长安的粮食布帛等物,大量增加,即所谓“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食货志》又载: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陕(治所在今河南陕县)、虢(治所在今河南省西部)、熊、伊、洛、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邵、卫(治所在今河南淇县)、汴(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许(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汝(治所在今河南临汝)等水次13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治所在今山西)、晋(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
由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不便于向京师漕运粮食,隋文帝“命宇文凯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隋文帝诏令在各地修建的储粮仓窖,规模甚大。据《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记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喜仓、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未有。”
上述著名大型仓窖,有的为隋炀帝初年所建。例如建于巩(今河南巩县)东南原的洛仓,筑仓城周回20里,穿3000窖,窖容8000石,可见仓窖容积之大。上世纪70年代在洛阳发掘的、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年的含嘉仓,已探出的粮窖有259个,大窖可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储粮数千石。在一个仓窖中,发现了距今1300余年的碳化谷子达50万斤。
《贞观政要·论贡赋》记载,据唐初人的估计,在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可见,隋王朝于建国后20年间所储备的粮食,竟如此之多!至于“得供五六十年”,有人理解为可供全国人民食用五六十年,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可能是说封建国家的皇室、官吏、军需等用粮,可供五六十年费用,而不包括生产粮食的广大农民用粮在内。即或如此,这样庞大的储粮数字,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贞观政要·论奢纵》又载马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对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段话:“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两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可见隋王朝的储备粮食,其数量确属惊人。
除国家设立的大型仓窖外,隋文帝还采纳了长孙平关于设置义仓的上奏。他说:“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丽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隋书·食货志》)于是,长孙平奏请诏令各如陌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于“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同上)《隋书·长孙平传》亦记载:“开皇三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闯巷,以备凶年,名日义仓。”
由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经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地所设立的义仓,后来果然在灾年发挥作用。当青、兖、汴、许、曹、毫、陈、仁谯、豫、郑、洛、伊、颎、邳等州发生大水,百姓饥馑之时,隋文帝命令苏威等人,“分道开仓赈给”,发挥了义仓的救灾作用。
隋文帝对于义仓的管理,非常关心。开皇十五年,隋文帝到东方视察,发现义仓的储粮“多有费损”。于二月下诏书说:本置义仓,止防7卜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同上)开皇十六年正月,隋文帝又诏令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同年二月,又诏令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后来,当各州发生灾荒时,无不充分发挥义仓的救灾作用。
隋文帝时国家储粮仓窖和各地义仓的普遍设置,致使储粮数量空前增加。储粮数额的空前增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仓窖的广设和储粮的遽增,是隋朝农业生产获得较大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各业并举,商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