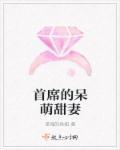456小说网>胡雪岩传奇电视剧在线观看 > 第26章 积德行善 散财广施庆余堂(第1页)
第26章 积德行善 散财广施庆余堂(第1页)
t杭州收复,市面逐渐繁荣。这时胡雪岩在杭州城里修建义渡码头,做了一件施惠于四方百姓的善举。
当时,杭州城外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与杭州隔江相对的绍兴、金华等通称“上八府”,这一带的人要到杭州城,必须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进城。从西兴摆渡过江,不管是“上八府”的人到渡口,还是下船上岸之后进城,陆路都要绕道而行,而从西兴到望江门码头,水路航运长,风浪大,很容易出事。胡雪岩在杭州长大,这些情况他当然是知道的。他早有开设义渡的想法,但在他开办自己的事业以前,自然不会有实力来完成这桩心愿。胡庆余堂开办时,他的资产已在数千万两白银,这时他做的第一件公益事业,就是摆义渡。他亲自勘选地址,亲自监督施工,在杭州三鹿庙附近江面较窄的地方,修起一座义渡码头,让过往的人直接由鼓楼就进城。而且他还出资修造了几艘大型渡船,既可载人,还可以载渡骡马大车。胡雪岩规定,所有客货过渡,全部免费。四方百姓无不拍手称好。
渐渐地胡雪岩做好事,已经变成一方土地的定例定规,饥荒战乱年景他设粥场、发米票,天寒地冻之时他施棉衣、舍棺材……直到他面临破产倒闭的那一年,也没中断。胡雪岩做的这些好事,使他在江浙一带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胡大善人”的名声。
胡雪岩为一个善人的名声如此地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要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去舔。”而且,“千来万来,赔本买卖不来。”散财施善,分文不取,用自己从刀头上“舔”来的血汗钱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名声,何苦来哉!如胡雪岩似的赚钱能去做好事、善事,实际上为许多生意人所不为。
然而,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这正显示出他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和眼光。他做好事,无疑有他行善求名,以名得利的功利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胡雪岩做的好事,也并不是与他的生意一点联系也没有。他修建义渡,实际上也就成全了他药店的生意。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药号建在杭州城里河坊街大井巷,原来光顾药店的多是杭嘉湖一带“下三府”的顾客。义渡在码头建成之后,从义渡码头到杭州城里必须经过河坊街。这义渡码头不仅为胡雪岩扬了名,而且也为来来往往的“上八府”的人直接到胡庆余堂购药创造了条件,等于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胡庆余堂的市场。不过,胡雪岩做好事,的确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就是因为“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因此,他做好事也是在求“市面平静”,也是他做市面的一种方式。
胡雪岩曾定免费施茶、送药的规矩。那是他在湖州大兴丝行开张后,七月里他到了湖州。一到湖州,他就吩咐他的丝行档手黄仪做一件能给人实惠的好事:时令在七月中旬,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节,丝行要在自己店前施茶、施药,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办。黄仪知道胡雪岩的脾气,做事要又快又好,钱上面很是舍得,于是当天就在大兴丝行门前摆出了一座木架子,木架子上放了两只可装一担水的茶缸,放在茶缸里的茶水还特意放了菊花、麦冬等清火败毒的药料。茶缸旁边放了一个装了手柄的竹筒当茶杯,路人可以随意饮用。另外,丝行门前还贴了一张广告,上写:“本行敬送避瘟丹、诸葛行军散,请内洽索取。”如此一来,丝行门前一下子热闹起来。
后来,施茶、送药成了胡雪岩丝行收丝时节必有的节目,而且还扩大到药店,实际上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杭州收复之后,胡雪岩开办了胡庆余堂,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以此赚钱万万不能,原因何在呢?
原来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战,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风餐露宿,又致大病缠身,这些都需用药。然而乱世流离,又有谁身上带钱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有不知?只是念及天下百姓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光墉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雪岩又派人送去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雪岩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了考官、士子们的一致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开店送药,送的只是“避瘟丹”“诸葛行军散”之类的普及型成药,花费不多,却具有两大重要意义:对施予对象而言,不论是清廷官兵,或是逃难百姓,无论如何,总是得到免费药品,对健康有所帮助;就胡雪岩而言,经由送药于人,胡庆余堂的名声得以远扬传播,声名传开之后,就可以和清军粮台打交道,建立正式的官商通道,把药直接卖到军队里去。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人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倚重的人物,由他负责经理赈抚局事务。
胡雪岩负责经理赈抚局事务后,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殓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因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从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淤泥。贫穷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步在泥沙中踉跄而行,时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恢复工捐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了1万两。
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说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署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托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获免。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一张广川被罚捐是否冤枉,因旁无佐证而无从考释,然而当时为富不仁的富商豪绅确也不少。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在一次上疏中就指责浙江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余人:“身拥厚赀,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无疑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掂量,与其当罪犯,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上述事务,人城后的胡雪岩仍代理藩库,各地解省银两非胡经手,省局不收。胡雪岩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固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那时他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得过他,还有啥靠不住的?
牌子做出来了,生意自然源源而来。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掠得的财物,从’数十两到十余万两不等,都存人胡雪岩的钱庄,胡雪岩借此从事贸易,设商号于各市镇,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家资已逾千万。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贾应有的道德风貌,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这类包含着辩证法的商谚,胡雪岩在饶有资财之后,也热心慈善事业,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