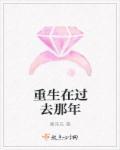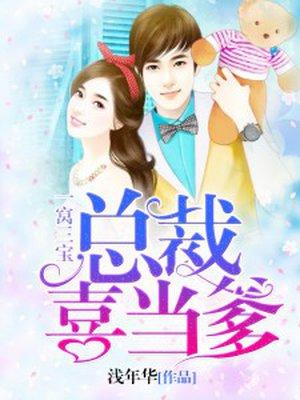456小说网>胡雪岩传奇电视剧在线观看 > 第26章 积德行善 散财广施庆余堂(第2页)
第26章 积德行善 散财广施庆余堂(第2页)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砝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足令今人感佩,引以为鉴。
广做善事,抛出银钱账,换回人情账。
说到底,处理好“银钱账”与“人情账”的关系,是为人处世中的必修课。在社交活动中,许多时候确实不能仅仅只在金钱上盘算自己的赚与赔。有时候你能凭着精细的算计获得二些蝇头小利但却很难有大的成就。相反,如果在金钱的赚赔上表现得很洒脱些、大气些,多在人情账的储蓄上下工夫,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而且往往是更大的、更长远的效益。
胡雪岩不在乎金钱上的赚赔出入,广做善事投入的人情账,等于在社会这个“大钱庄”的储蓄,使他获得更广大的承认,社会上的巨大影响,让许多人十分佩服他的大气和远见。
假如胡雪岩只盯着自己银钱上的进出而一毛不拔,或为自己多留一点或一毛分成几段拨,也许就会出现钱财账有了盈余,人情账却欠下了一笔,从此永无翻身之日。这难道不是得不偿失吗?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胡雪岩还有着“责人宽,律己严”的博大胸怀。同样是对待钱财和人情的问题,如果生意中胡雪岩亏了,他会大度地将其化做人情;但如果生意中亏的是朋友、是对方,他一定会坚持“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全力给对方弥补生意中的亏损。这也是他的信用的一个重要体现。胡雪岩这样的做法,使得生意伙伴与他做生意时无形中在利益分配上获得了一种安全保障。因此,胡雪岩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合作伙伴及朋友间必要的信用保证。
胡雪岩做生意时特别注意不拖欠别人的人情账。比如胡雪岩与庞二合作,在做第一笔生丝“销洋庄”的生意时,发现了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的“毛病”。胡雪岩不仅想方设法收服了朱福年,十分圆满地处理了因为朱福年而在生意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显示出了自己十分精明的生意眼光和为人仁厚的品行。庞二因朱福年这件事,对胡雪岩的为人,由了解而到心悦诚服。因此,他想与胡雪岩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让胡雪岩完全加入自己的生意,帮自己全权照应上海的丝行。庞二送胡雪岩股份,算是胡雪岩跟他合伙,这样胡雪岩也就有了老板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为他管理上海的生丝生意了。
对当时刚刚进入丝业的胡雪岩来说,能够与丝业中的巨头庞二合作,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胡雪岩却并不想因为贪图钱财的盈余,而欠庞二的“人情账”。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吃“干股”,既然庞二同意让他人股,他就必须拿出现银做股本。胡雪岩实力不如庞二,可以只占两成,庞二拿四十万,他拿十万,而且一定要立个合伙的合同。此外,不能仅仅自己在庞二的生意中参股,胡雪岩的生意也一定要让庞二占同样的股份。胡雪岩的想法十分明确,朋友之间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不能欠下人情账,更不能生意、感情不分,一概而论,搅在一起纠缠不清。
胡雪岩能够这样处理这件事情,自然是高明的。从合作的角度,胡雪岩拿出这十万现银的股本,与庞二订立了合同,双方之间就明确了责任和信用关系,而这一种朋友关系之外商业上的责任信用关系,正是朋友之间生意能够长期合作的保证。
在实际中,生意伙伴之间也的确需要信用的保证。这种保证当然可以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朋友感情彼此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但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生意场上仅有感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感情之外的“按规矩办”——签订合同文本的保证。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亲兄弟,明算账”,说的就是感情、生意要分开而论。这句话的确是商场中应该遵循的至理名言。
胡雪岩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牢牢地抓住了“钱财账”与“人情账”之间的辩证关系,不重此轻彼,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全根据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条件区别对待,能够恰到好处地处理好“钱财账”与“人情账”的关系。有取有舍,能宽能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清代末年盛极一时的大商巨贾胡雪岩成功的基础。
胡雪岩的裕记丝行档头朱福年吃里扒外。朱福年为人做事十分不地道,不仅在销洋庄的事情上暗中作梗,而且还拿了东家庞二的银子“做小货”,庞二自然不能容忍。依庞二的想法,一定要彻底查清朱福年的问题,并狠狠地整他,然后将他扫地出门。但胡雪岩却觉得这样做事太绝,不妥当,他说:“一发现这个人不对头,就彻查,请他走路,这是一般人的做法。最好是不下手则已,一下手就叫他晓得厉害,心生佩服。要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使人心服口服。‘火烧藤甲兵’不足为奇,要烧得让他服服帖帖,死心塌地为你出力,才算本事。”胡雪岩先通过关系,把朱福年在同兴钱庄所开“福记”账户历年进出的数目,将丝行的资金划拨“做小货”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再到丝行看朱福年做的账,并在账目上点出朱福年的漏洞,“有没有错,要看怎么个看法,什么人来看。我看是不错,因为以前的账目,跟我到底没啥关系,叫你们二少爷(庞二)来看,就是错了。你说是不是呢?”胡雪岩仅仅是点到为止,并不点破朱福年“做小货”的真相,也不再加以深究,让朱福年感到自己“做小货”似乎已经被抓到了“把柄”,但又摸不着头脑,觉得自己成了“孙悟空”,无论怎么跳也跳不出胡雪岩这尊“如来佛”的手掌心。只有主动认错,表示服帖,才是上上大吉。
“胡先生,我在裕记年数久了,做事记账手续上难免有疏忽的地方,一切要请胡先生包涵指教。将来怎么个做法,请胡先生吩咐明白,我无不遵办。
朱福年的话里带有歉意。很明显,这是递了“降表”。到此地步,胡雪岩便开门见山地直接说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福年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二少爷既然请我来看账,自然对他要有个交代。你是二少爷的大档头,是这爿店里抓总的,我只要跟你说就是了。下面各人的账目,你自己去查,用不着我插手。”
“是。”朱福年见有补救的机会,连忙说,“我从明天就清查各处的账目,日夜赶办,有半个月的工夫,一定可以盘查清楚。”
“好的。你经手的总账,我暂时也不看,等半月以后再说。这半个月之中你也不妨自己先查点一下,如果还有疏忽的地方,想法子弥补,我以后仅仅是看你几笔账。”接着,胡雪岩清清楚楚说了几个日子,都是从同兴钱庄那份“福记”收支清单中挑出来的,都是一些有疑问的日子。
朱福年暗暗心惊,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知道,却不明白胡雪岩何以了如指掌,莫非裕记中有他的眼线?照此看来,此人高深莫测,以后万万不可大意。到了这个地步,朱福年算是彻底服了胡雪岩。不过,这时的“服”,还是被胡雪岩的气势所威服,以害怕的成分为多。
朱福年心中的所有疑惧都流露在脸上。胡雪岩索性开诚布公地说:“福年兄,你我初次共事,恐怕你还不大晓得我的为人。我一向的宗旨是‘有饭大家吃,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所以,我决不肯轻易地敲碎人家的饭碗。不过做生意跟打仗一样,总要同心协力,人人肯拼命,才会成功。过去的都不用说了,以后看你自己。你只要肯尽心尽力,不管心血花在明处还是暗处,说句自负的话,我都一定能够看得到,也一定不会埋没了你的功劳。二少爷面前我一定会帮你说话。也许,你倒看得起我,将来愿意跟我一道打天下。只要你们二少爷肯放你,我欢迎之至。”
于是,胡雪岩特意留出一些时间,让朱福年暗中查点账目,自己慢慢弥补过失,等于有意放他一条生路。最后,态度十分明确地告诉朱福年,只要尽心尽力地去做事,他仍然会得到重用。这一下朱福年对胡雪岩的宽宏大度真就感激不尽了,彻底服帖了。
胡雪岩的做法,实际上是从嵇鹤龄讲的一个故事中获得的启发:苏州有一家南北货行,招牌叫“方裕和”。“方裕和”从两年以前就不断地开始发生货物失窃走漏的事情,而且丢失的都是鱼翅、燕窝、干贝之类的极其贵重的海货。方老板不动声色,明察暗访,很长时间才弄清,原来是自己向来最信任的一个伙计,也是自己的亲戚与漕帮勾结,将贵重海货捆绑在店里出售的火把中偷出去,再运到外阜脱手。难怪他在本城同行、饭店中竟然没有查到吃黑货的任何线索。在方老板的逼问下,伙计承认了偷窃行为。按规矩,自然要请他走路。但方老板却以为能够“走私”两年之久而不被发现,此人一定有相当的本事。再说是店内同伙勾结,宣扬开来要开除一大批熟手,还有损自己的信誉。最后不仅没让这个伙计“走路”,还加他的薪水,重用了他。这样一来,那伙计发自内心地对宽恕自己的老板感恩图报,尽心做事,自然不会再干偷货走私的事情。
那老板的做法,胡雪岩也认为相当漂亮,但他认为火候还差那么一点儿。他对嵇鹤龄说:“照我的做法,只要暗中查明白了,根本无须说破,就升他的职,加他的薪水,叫他专管查察偷漏。”胡雪岩的理由是,做贼是不能让人拆穿的,你一拆穿就落下痕迹,无论如何他和别人都相处不长。既然他是个人才,自己又能容留他,又何必一定要拆穿他,只让他感恩就行了。胡雪岩对朱福年,就是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