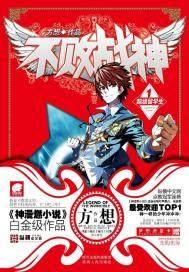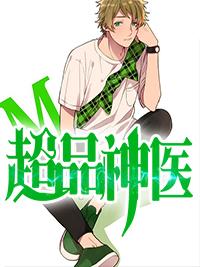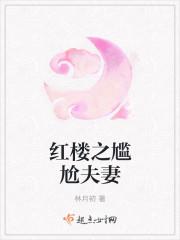456小说网>当官必读曾国藩 > 下篇 胡雪岩的做事绝学(第3页)
下篇 胡雪岩的做事绝学(第3页)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10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面子就是招牌
胡雪岩特别重视面子,即使在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之时,他也不忘记要保住面子。
他曾说过:“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所谓“守信计”是指: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由此看来,胡雪岩对“以逸待劳”深刻的经商作用,真是大悟彻悟!
上海阜康挤兑风潮,第二天就波及杭州。胡雪岩从上海返回杭州,还没有下船就得到了消息。而得到消息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把面子保住。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所有一切排场照旧。胡雪岩一到杭州,就有在胡家地位特殊的乌先生上船接住,报告上海、杭州两地的“灾情”,同时他建议胡雪岩移舟到离家更近的万安桥登岸;胡雪岩的宅第在元宝街,他的钱庄在清河坊,因此,胡雪岩由外地回杭州,一向是在位于元宝街与清河坊之间,也是杭州城里最热闹的望仙桥码头上岸。而且每次回杭,都要家人接轿,摆出极隆重的排场:身穿簇新“号褂子”的护勇在码头上站成两排,点起官衔灯笼,打起旗子,护着一顶蓝呢大轿,常常会引来大群看热闹的行人。乌先生的建议自然是因为风潮已起而希望胡雪岩不要过于张扬。但胡雪岩没有接受乌先生的建议,而且要求一切排场照旧。这当然是在保住面子,胡雪岩不能让别人以为阜康挤兑风潮一起,他自己就灰溜溜的了。
第二,阜康营业照旧。胡雪岩一到钱庄,就否定了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商量的钱庄停业三天的决定,要求照常卸下排门做生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谢云清连夜察看储户账目,做这两件事情,一是提早将几个大户的利息结算出来,把银票送到他们门上去;二是告诉那些大户,年关已近,要提款应付开销的,尽可交待,以便预先准备。这是守信用,更是要做回面子。阜康因为贴出停业三天的告示,已经在杭州城里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没有引出更严重的后果,但一遇风潮便缩头停业,事实上面子已失。
第三,原拟要办的三女儿的喜事也照旧。胡雪岩此次从上海回杭州,其实主要就是为三女儿的婚事。虽然还未下船就知道了要命的“噩耗”,但胡雪岩一进家门,就告诉螺蛳太太,女儿婚事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一切照常。而且,再难也要做到,不管用什么办法,场面无论如何要绷起来。这当然更是做面子。阜康挤兑风潮一起,是否仍按以前排场大肆操办女儿婚事,正是为众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如果女儿的婚事一改原来胡家办大事的排场风光,自然更是没有了面子。胡雪岩不能“丢”面子。
胡雪岩如此处置,当然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硬撑。
他如此处置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这些措施使客户保持了对于阜康的信心,由此稳定了人心并保住了自己的信誉。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措施,杭州的挤兑风潮在开始的时候才没有恶性发展。第二,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大户,使原本可能参加挤兑的大户不再加入挤兑风潮,减少了压力。钱庄生意最怕挤兑,挤兑最烈则是大户加入兴风作浪。大户稳定下来,零星散户,力能应付,也就不足为虑了。
这是胡雪岩危机中力挽败局的重要手段,只要在人们心中阜康的招牌不倒,自己的场面就可以撑下去。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钱财即使再多,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留下的,只是一个生前和身后的名。
有一次,有位同仁向胡雪岩请教人生哲理和做生意的经验,胡雪岩说:“人生世上应该先求名,还是先求利?……别的我不知道,但做生意是要先求名,不然怎么叫‘金字招牌’呢?……这话大有道理,创出金字招牌,自然生意兴隆通四海,名至实归,莫非名利就是一样东西?”
生意场上,求名是为了求利。自我形象树立起来了,名气做响了,“金字招牌”擦亮了,生意也就自然会兴隆起来。这就是所谓名至实归:名声扬起来了,自我形象好了,那么财富就会落入你的怀中。
事实也的确如此,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无形的资本也可以创造利润。良好的形象就是企业的无形资本。
杜邦公司的兴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杜邦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采用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
1936年9月,杰西建立了杜邦财团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尼莫尔基金。两年后,一所三层楼的医院在离威尔明顿不远的尼莫尔庄园中的22英亩空地上破土动工了。从此该院驰名于世界。到1963年为止,这所医院为残疾儿童免费治疗各种病例达50万人次。
办这所医院是杰西的主要活动。这一活动,与她把5500万美元赠给学院、大学以及像斯特罗姆、瑟蒙德基金会一样,都表明了杜邦财团慈善的一面。
19世纪以来100多年里他们积累了巨额的家庭财富,但也引起了一连串的骂名。有人说杜邦可能是美国人最痛恨的名字。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给杜邦带来了数不清的财富。
为了重新塑造杜邦的良好形象,杜邦家族采用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根据这一思想,杜邦的宣传对象主要有三种:
(1)雇员、顾客、股东、供应厂商、企业协会、工厂所在的城镇;
(2)作家、新闻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大学知识分子;
(3)政府官员。
以上这些人员或多或少都对杜邦有所了解,再集中在他们身上大做宣传,那么根据布雷曼的估计,由杜邦公司通常广泛发布的消息所引起的“公众”效应的微波就会变成巨浪。布雷曼回忆说:“在几百万人的心中造成了一个新的印象,它为我们找到了新的立足点。”
皮埃尔还在杜邦家族开创了一个良好的传统,积极向教育界捐款,杜邦家族成立了专门的家族基金会向美国经济特权阶层的教育事业提供捐款。仅在1966年一年内,小伊雷内·杜邦就向宾夕法尼亚的公立学校捐赠了50万美元,向布林·马尔学校捐赠了30万美元,向特拉华的航空学院捐赠了9。4万美元。在特拉华,杜邦家族也向特拉华工学院捐款。光皮埃尔一人就向特拉华的公立学校资助了1200万美元。杜邦家的人给学校捐款的目的很单纯,那就是让孩子们从小就形成一种意识,杜邦是一个很友善的名字,是一个名气响亮的企业。
无独有偶,比杜邦公司早一个世纪的胡雪岩也是一个善于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的精明人,并为之而不遗余力,丝毫不比杜邦家族的人逊色。
胡雪岩在阜康钱庄开张之初时通过认购户部官票,树立了钱庄的良好形象,实在在地实现了名声扬起、实利落怀的效果。
而胡雪岩的药店胡庆余堂则更是如此。由于胡庆余堂在创业时期就定下的以诚实无欺做名气的宗旨,也由于胡雪岩向有病无钱的穷人免费送药和向军营捐药的两招,使胡庆余堂很快就名声大振。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经营也一直旺盛不衰,遇到春夏时疫流行的季节,上门的主顾常常排起长龙等药,胡庆余堂自然也是大为赚钱。胡雪岩的生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走向衰败,最后全面倒闭,他的其他生意如钱庄、典当、丝行以及私人财产如房产、田地,后来都落人他人之手,唯有胡庆余堂却完整地保留不动,实际上也是胡雪岩彻底衰败之后,为他保存了一笔不菲的家业。
究其原因,与他在药店生意上做出的名气,与胡庆余堂的“金字招牌”有着很大的关系。就连他的药店档手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在阜康发生挤兑风潮且开始波及胡雪岩的其他生意,败局已定,胡雪岩面临查封家产的时候,他的药店档手为安抚店员所做的分析,就很有道理。他对店员们说,胡大先生办得顶好的事业,就是这胡庆余堂。胡庆余堂不仅赚了钱,也为胡大先生挣得了好名声。如果说亏空了公款,要拿胡庆余堂抵债,货色生材都可以人官,但这招牌是不会被摘下的。胡庆余堂如此大的名声,官府一定不会将它封掉,胡大先生也仍然是胡庆余堂的大老板,药店档手要求店员要格外小心,照常经营,抓药要地道,对待客人要和气,这只饭碗一定捧得实,不必担心。
这就是所谓名至实归!名气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名气的效果能够发挥到这个份上,也算是一种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