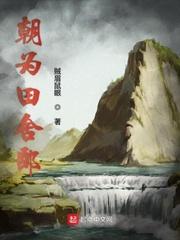456小说网>垂耳执事95微博图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陆上锦摔门而去,坐在车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直到嗡鸣的太阳穴被尼古丁彻底麻木镇静。
言逸惊惧哀求的样子又浮现在脑海中。
陆上锦按着心口,趴在方向盘上忍着心口急剧的痉挛跳动,双腿冰凉麻木,甚至踩油门时都没什么知觉。
这大概是他活到这么大体验到的最淋漓尽致的狂躁暴怒。
此后两天,陆上锦都在公司里过夜,没再回过家。
办公桌上堆的合同大多签完了,剩了一摞久安鸿叶的合同,陆上锦没有半点心情翻开,索性一直搁置。
久安鸿叶的副总起初打来电话问了一下,察觉到不对劲儿以后不敢再问。
会议结束,夏凭天从会议室出来,脸色黑得像块炭。
陆上锦到底在折腾什么,这是在针对他们鸿叶夏氏?拖着好几个合同快逾期了也没动静,在干什么?
他爸留下的那孩子该着了短命,多脏器衰竭,谁救得回来?他他妈是皇帝老儿救太子呢?不至于要鸿叶夏氏跟着陪葬吧。
越想越憋气。忍不住给陆上锦打个电话,他要是再不接,立刻让司机开车往长惠去。
响了十声陆上锦才接起来。
夏凭天忍着火儿,跟陆上锦好言好语问了问。
陆上锦淡淡问:“你是不是帮你弟弟找过言逸。”
“啊?没有啊。”夏凭天噎了一下,他确实帮夏镜天查过,但他应该没做什么吧。
“你有个好弟弟。”
陆上锦挂了电话。
夏凭天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一把抓住助理的领口:“去,把陆上锦上次带人去检查的报告调来给我看。”
他气急败坏地扯掉领带,下楼开车去了夏镜天的学校。
夏镜天平时懒得回家也偶尔住寝室,门禁大爷没拦住夏凭天,让他带着几个alpha闯上了宿舍楼。
这些天夏镜天确实懒得回家。
他从颓圮酒吧回来以后就一直窝在学校不怎么动弹。
另一个室友伏案画工图,他就靠在床里拿着一个旧笔记本发呆。
他从颓圮酒吧的二楼卧室里把这本笔记带出来,至今已经翻看了好几遍。
那只小兔子的笔迹和他人一样清秀。
笔记本上除了在边角记录一些备忘的事宜,绝大多数都像日记一样记录着或开心或不开心的生活,和陆上锦相关的事情后边总会写上分数。
一页页看下来,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孤独。
明明分数已经减到负数了,一句“带你回家”又把分数加满。
平淡无奇的小事塞满了整个笔记本,夏镜天就像陪着少年时的小兔子走过了一个十年。
“镜天你……没事吧?”室友放下勾线笔匆匆走到夏镜天床边,夏镜天屈着一条腿沉默地靠在枕头上,双眼皮有些肿,眼睛红着,无精打采。
“你有没有喜欢到远远看着都觉得很心疼的人?”
室友微张着嘴,摇了摇头。
寝室虚掩的防盗门被一脚踹开,伴着一声砸门的巨响,夏凭天气势汹汹走进来,几个魁梧的保镖冲进来把室友带了出去,带严了门。
寝室里只剩下兄弟二人。
夏凭天一把扯住他弟弟的手臂,狠狠把人从床上拽了下来,扬手抽了一巴掌,咆哮道:“把你能的!可以啊,把别人媳妇玩儿到假孕,好的不学坏的学,你行,我他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他收着手劲儿,夏镜天仍旧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巴掌震住了。
“你喜欢那小兔子是吧?”夏凭天把一摞检查报告拍在夏镜天手里,“看看你把人家害得多惨,假孕强制流产,陆上锦亲自动的手。”
夏镜天咬着牙低头浏览检查报告,确诊假孕四个字刺得眼睛疼。
强制流产?
他该有多疼多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