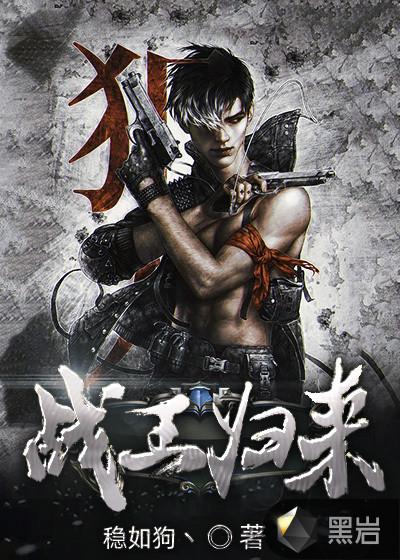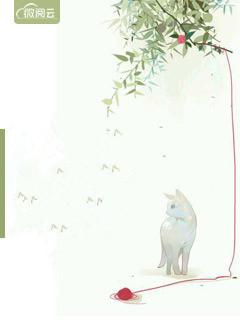456小说网>中华取名艺术大全 第2章 > 第4章 名目繁多别有寓意(第10页)
第4章 名目繁多别有寓意(第10页)
这话似乎说得有点奇怪,应稍加说明。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有的作者性格特别,他文章是要写的,但不想就此扬名,因而有意隐姓埋名,示人以不可测;也有的作者因视某些文章为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名堂,但能换几块稿费还是好的,于是随便化上一个笔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求闻达”。
作者使用笔名有着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使用笔名的好处是隐身、灵活、便捷。笔杆子爱用笔名,这是文坛的一种特殊现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三、笔名的类型
作家成百上千,笔名自然五花八门。如果做一个分门别类,总的说来大体上有这样两种类型。
1.以姓名方式出现的笔名
例如:周绍仪,笔名周立波。
吴熙成,笔名吴伯萧。
郭恩大,笔名郭小川。
马千木,笔名马识途。
余昭明,笔名叶紫。
万家宝,笔名曹禺。
蒋海澄,笔名艾青。
林觉夫,笔名秦牧。
杨凤岐,笔名欧阳山。
2.以非姓名方式出现的笔名
例如:柳亚子,笔名青兜。
赵平复,笔名柔石。
闻一多,笔名夕夕。
许地山,笔名落华生。
钱钟书,笔名中书君。
比如作家丁玲,本姓蒋。久而久之,她不胜其烦,她只好用姓,却又嫌“蒋”字笔画太多,不好写,就找了个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作为姓氏。至于玲字,就像她本人说的:“‘丁玲’毫无意思,只是同几个朋友闭着眼睛在字典上各找一个字作名,‘玲’字是我瞎摸的。”像丁玲这样靠“瞎摸”字典拟定笔名的人不少。
也有的人虽然不“瞎摸”字典,那笔名的得来也是一种巧合。例如李尧棠,行世的笔名是巴金。这笔名是如何得来的呢?巴金说:
“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思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为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一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这本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
从“巴金”这个笔名的由来可以看出,“巴金”和“丁玲”的拟定方法,惟一的区别就是是否查过字典。那种认为“巴金”是从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个名字各取一字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鲁迅先生一生使用的笔名最多,其中多数与本名无关,而且多数是含有某种意义的。我们试析如下:
鲁迅:鲁迅先生的母亲姓鲁。至于迅字,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就是承迅行而来的”。“迅行”是鲁迅早期用过的笔名,意即迅猛前进。鲁迅先生曾对许寿裳说,鲁迅就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那种引据《尔雅》释“迅”为“狼子”的意见,未合鲁迅先生的本意,不足取。
丁萌:“叮虻”的谐音。这是鲁迅1933年5月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新药》时使用的笔名。鲁迅在5月4日给该报编辑黎烈文的信中谈到:“……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可见其使用这个笔名时的心境。
封余:1928年8月,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错误地攻击鲁迅先生为“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接过这个“谥号”,压缩成“封余”二字,用做笔名以回敬对方。又进而变为丰瑜、丰之余、唐丰瑜等。
公汗:1934年5月20日写《偶感》时,联想到潘公展主办的《汗血月刊》,索性以“公汗”为笔名,聊以调侃。
何家干: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名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家’作谁家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这个笔名看上去是随手拈来,没有含义,但干字的使用则不寻常,一个干字的使用,使笔名带上了斥责反动派的内涵。这个笔名鲁迅先生用的次数很多,可见他本人也喜欢这个笔名。
及锋:这是鲁迅1934年9月29日在《中华日报·动向》批评林希隽时使用的笔名。林希隽名“希隽”,鲁迅读“隽”如“镌”,便以“及锋”相对。以对仗的方式取笔名是鲁迅的癖好。如文中提到《庄子》的“养生主”,就以《庄子》的“齐物论”为笔名。
康伯度:英语comprador的音译,意即买办。是敌人对鲁迅的攻击,鲁迅随手拈来而已。
倪朔尔:“鲁迅”的英译为Lusin,将其颠倒便是Nisul,音译为汉语便又成为“倪朔尔”。
且介:即“租界”二字去掉偏旁。鲁迅的集子也有《且介亭杂文》。
孺牛:摘自己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为笔名。
隋洛文:1930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先生又接过敌人“所赐之谥”,改造成“隋洛文”,用做笔名以回击敌人。又进而变为洛文、乐贲、乐雯、洛、乐文等。
韦士繇:即“伪自己”的谐音。鲁迅的集子也有《伪自由书》。
越侨:鲁迅乃浙江绍兴人,多在上海、北京等地生活,故以此来命名。类似的笔名犹有燕客,谓客居北京;越客,谓来自越地之游客。
中头:1934年6月16日发表《玄武湖怪人》按语时,因其文中有“小头”、“大头”之称,故取笔名中头。